

每個村落都是一座文化堡壘
小時候,,覺得世上最難逾越的是“說話”。語言的障礙比攀登還難,。趕集,,經(jīng)常遇上對方操著一根生硬的舌頭在比劃著,別扭的同時,,感覺對方很遙遠(yuǎn),。聽大人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說曾有一個說客家話的人和一個說閩南話的人趕集半路相遇,,一個想買對方的小豬,,一個說五五二十五,另一個也說五五二十五,,結(jié)果兩人越說越激動,,如同吵架,卻根本不知對方說了什么,,好像嗓門低就吃了虧似的,,他們,互相朝對方吼山似的臉紅脖子粗了半天,,其實他倆說的是同一個價,。
小時候,我生活在閩南話與客家話交匯地帶,。我們那小村莊說的是客家話,,相鄰幾個大村莊說的都是閩南話。那時人的交流很少,,一年到頭家里難得見幾個生人,,也就逢年過節(jié)串個親戚,人的活動很少超出村莊,。遇上閩南話的客人,,我總覺得他們不是“同類”,。要命的是,上學(xué)時,,老師竟然用普通話與閩南話對譯課本,,讓我根本找不著北。從一年級到三年級,,每天看著老師兩片嘴皮翻飛,而我,,卻根本不知道老師在講啥,,每天都像一個小呆瓜坐在課堂上不知所云。成績就不用說了,,總是個位數(shù),。直到四年級,我和幾位說閩南話的同學(xué)玩在一起,,讓我聽懂了他們說的話,,進而讓我聽懂老師的課,讓我漸漸明白了課本上的內(nèi)容,。
方言的障礙讓我深受其害,。然而,南方似乎是方言的沃土,,翻過一座山,,或渡過一條河,你就會落入陌生方言的包圍中,。當(dāng)你發(fā)現(xiàn)整個村莊操著濃濃的異腔,,仿佛到了“番邦”,語言像山一樣橫亙著,,一時難以逾越,。細(xì)心的人會發(fā)現(xiàn),不止是方言,,在南方,,雞犬相聞,遙呼相望的兩個村莊,,不但語言不通,,連習(xí)俗也大相徑庭。我們村過七夕,,翻過一座山的姨媽家卻沒有;同樣,,他們村過七月十五,我們村卻沒有,。這是多么有意思的差別,,然而,正是差別,才顯得豐富多彩,。
語言和習(xí)俗都是文化的活化石,,細(xì)細(xì)探究,仿佛看到一條歷史的河流緩緩流動,。華夏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一個人口南遷歷史現(xiàn)象特別凸顯。這種南遷現(xiàn)象還被史學(xué)家們稱之為客家遷徙,。西晉以來,,由于兵燹、災(zāi)年或人口膨脹,,先后發(fā)生了五次大面積客家人南遷,,這些原本定居在中原的漢民,被迫舉家舉族外遷,,背井離鄉(xiāng)尋找一個可供生息的土地,,以躲過災(zāi)年。遷徙的大軍從不同地方走來,,向不同的地方走去,。但大方向還是有的,就是要向著大山走去,,向著戰(zhàn)車再也不能馳騁,,戰(zhàn)馬再也不能馳奔的地方走去。像磁針引路似的,,他們,,都一路向南走來。這些遷徙的平原先民們急匆匆地往前趕路,,肩上扁擔(dān)累彎了腰板,,一抬頭,突然看見已陷入綿綿群山包圍之中,,煙霧迷離中,,看不清來路,也看不見前方路在何方,,拂手拭一把額頭汗水,,卻被山風(fēng)灌個滿懷,一拍腦門,,這草木豐沛的群山不正是最好的屏障么!從此停下疲憊的腳步,,夯土為樓,焚茅開荒,,開始新一番生息繁衍,。要不然,,千山萬壑中,為何都有中原先民后裔,。南方村落中,,往往是一個或幾個姓氏聚居,絕不會是眾多姓氏混雜,。姓氏就是氏族的血脈徽章,,它讓人一目了然看清基因紐帶的脈絡(luò),每一個村落的姓氏都亮明你的前生與來路,。
人口的流動帶來了文化的碰撞,。這些遷徙的族群就像一顆顆文化的種子,把起源的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一步步向南傳播,直到天涯海角,。每到一處,,中原先進的農(nóng)耕文化,耕讀傳家的思想,,都能落地生根,,并與當(dāng)?shù)赝林牟粩嗯鲎踩诤现校纬瑟毺氐牡赜蛭幕蛘f文化現(xiàn)象,。所謂十里不同俗,,細(xì)究之,他們又似曾相識,,個中原因,,就是地域演變的結(jié)果。南方多山隔阻的原因,,讓這種地域風(fēng)格更加鮮明,。也正是高山大河的隔阻,讓一個地方的語言和習(xí)俗從此放慢或停下前進的腳步,。一種方言,,或一宗民俗往往是幾百年甚至是上千年前的文化孑遺。從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看到,,每一個村落都是一座文化的堡壘,。
只是,方言與習(xí)俗都是有年輪的,,語言和習(xí)俗都是活化石,,歷史總在路上等我們,我們每天都在和古人相遇,,只是自己不知道,。歷史不只是在博物館,,更在我們嘴上,在每個人身上,。我們身上流淌著古人的全部文化基因,,它在我們當(dāng)今的語言中,在各地的習(xí)俗中,,我們自身就是一座文化基因的博物館,,卻從未發(fā)現(xiàn)。我們操著古老的鄉(xiāng)音,,在與今人對話,,還將與后人對話,方言和習(xí)俗是最清晰的歷史鏈條,,橫貫古今,,它需要我們拿出全部的熱情去傳承和發(fā)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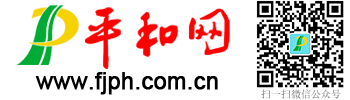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