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 音

一
中秋一過,平和縣城大街小巷社戲就火熱開鑼,一直到年關(guān)都到處鏘鏘滾。漫步街頭,,聲振云霄的鑼鼓聲一響,,如帛如絲的弦竹聲馬上連成一片,,隨即生旦凈末丑一一開腔,,那高低錯落的唱腔如潮水般洇過來,平靜的街頭巷尾,,頓時被這種嚨咚嗆咿咿呀呀的大班戲鋪排得滿滿當(dāng)當(dāng),。這些古老的戲劇雖不受當(dāng)下年輕人追捧,但對發(fā)燒友和上年紀(jì)的老年人來說,,這絕對是每年一遇的文化大餐,。他們不習(xí)慣那直白式的流行樂,而這反復(fù)捶打過的戲詞,,再依著腔調(diào)唱出來,,就像煮熟的糯米經(jīng)過反復(fù)舂打,,然后再依大小摶成圓子、糯糕,,圓潤而富有彈性,。那腔調(diào)一亮出來,絲絲入扣,,聲聲入耳,,穿街繞巷能飄出十里開外。
我熟悉這種聲音,,童年不知跟祖母趟過多少戲場,,聽得耳朵都起繭了,,戲中的唱腔與曲調(diào)早已刻錄在記憶深處,,不管是薌劇還是潮劇,一杵鼓起,,左右文武兩班樂片一響,,那綢緞般腔調(diào)一層層鋪排開來,童年的景致便潮水般漲起來,,刷刷地沖擊記憶的沙灘,。
一杖馬鞭輕揮,繞臺幾圈,,長亭與短亭,,兜兜轉(zhuǎn)轉(zhuǎn)數(shù)千里;再一通鑼鼓齊鳴,幾易背景,,又是幾度春秋,,紅顏少女成老婦。臺上一嗓子亮出來,,臺下的祖母便中盅似的走入劇中,,如醉如癡,整個魂兒便飛到臺上去,,飛進她的劇里,,不到曲終人散,你拉也拉不動她,。“做戲狂,,看戲瘋”,祖母是出了名的“戲瘋子”,。
方圓十里,,不管哪個村社演社戲,她都一場不落。特別是潮劇,,她甚至稱得是上骨灰級的發(fā)燒友,。許多劇目一演再演,她早已熟爛于心,,即使同一臺戲同一劇目從張村到李社再到王莊像酷狗單曲循環(huán)一樣,,不斷地重復(fù)演出,她也照樣看得有滋有味,,直到這劇團走出老遠(yuǎn)的地界才作罷,,追戲成了她最熱衷的一件大事。這些遛了再遛的戲目,,一登臺她便能從唱腔,、道白、行頭,、臺步,、聲色品頭論足一番。
鄉(xiāng)下流行串場看戲,,每年村里唱社戲,,十里八村的姑姨舅表都會來看戲。社戲,,往往也成了親朋間相互走動,、拉家常、聯(lián)絡(luò)感情的一座橋,。夜深露重,,主人家還會備下宵夜讓客人充饑、御寒,。每個村都有自己固定演社戲的日子,,祖母沒等人家邀請,早在日歷上記好日子,,掐著指頭一天天算過去,。等到好戲開鑼那天,還沒挨到太陽下山,,她便梳洗完畢,,急匆匆趕往親戚家。出于禮貌,,她會象征性地小坐片刻,然后,,直奔戲場,在戲臺前占上好位置,如若磐石地杵在那里,,直到半夜戲演完了,,臺下人都散場了,她才漸漸回過神來,,然后一把拉上我的小手,,跟著祖父一道踏月而歸。夜宵,,她一次都沒吃過,。
我不是戲迷,誘惑我去看戲是因看戲時能買的零食,,瓜子,、蜜餞、糖果,、餅干,,夏天還能帶上清涼可口的雪糕。那時尚小,,看不入戲,,最不解的是,就那么一句詞,,甚至一兩個字,,臺上小生或小姐竟一步三搖,連比帶劃咿咿呀呀地唱上大半天,。瓜子都嗑了大半包,,甚至溜一圈回來,一看,,還是剛才那張面孔在那兒咿呀個不停,,真煩人??偸菓蜻€沒結(jié)束我就睡著了,,每次都是祖父和祖母輪流把我背回家。我不解,,這么悶的戲,,祖母為何看得有滋有味,并且還會在臺下?lián)u頭晃腦地小聲哼唱,。她那對眼睛直直地盯著臺上,,閃著異樣的光彩。臺上的一顰—笑,,一嗔一惱,,都時時寫在她臉上,。我仔細(xì)看臺下祖母,她那張老臉如幕布上臺詞,,時時在變化中,。總是在這時候,,我常猜想,,若她年輕時上臺去唱,那勻稱的身板,,那精致的五官,,再加上那雙杏眼流波能左右顧盼的眼睛,那絕對是最好看的“崔鶯鶯”那類女角,。
那次,,聽說潮州一位名旦要來人民劇場演出,仿佛中了大獎似的,,祖母興奮不已,。買菜時,每天都拐去劇場探看海報張貼出來了沒有,。那天傍晚,,她剛好從劇場路過,看見海報終于張貼出來了,,她一路小跑回家,,氣喘吁吁地對我說:“乖仔,潮州的那個旦角來了,,晚七時要演《陳三五娘》,,快來不及了。”說完,,她開始火急火燎地做飯,,也不等祖父收拾停當(dāng),祖孫倆胡亂扒拉了幾口,,就飛快地朝劇院奔去,,把祖父一個人丟在家中。
一路看表,,一路小跑,,祖母不斷地催促我大步快走,我的手都被她拽得生疼,。緊趕慢趕,,終于提前一刻鐘趕到人民劇院門口。奇怪的是,,劇院門前竟空無一人,,祖孫倆一臉錯愕,。我抬頭看那張海報,發(fā)現(xiàn)戲要明晚才上演,?;叵雱偛乓宦纷汾s的瘋勁,頓時,,我倆都忍不住笑了起來。翌日,,自然又是祖母和我及祖父三人最先趕到劇場,。不要說潮劇名旦要來,其實就是從潮州隨便來個戲班,,祖母的魂也就跟著飛了,,那是她的命,她的根,。因祖母不是本地人,,她來自潮劇的故鄉(xiāng)——潮州。
二
1939年夏,,侵華日軍攻占潮汕,。戰(zhàn)火之中,命如累卵,。家里女人家都不敢出門,,更不敢上街,甚至要藏在閣樓頂,。萬不得已要出門,,也是滿臉涂鍋灰,把自己弄得蓬頭垢面,,奇丑無比,。
戰(zhàn)亂一時難以平復(fù),藏又能藏到何時了,。迫于時局,,當(dāng)時許多潮汕人四處逃難。婦女們更是驚弓之鳥,,能逃的都逃出來,。鄉(xiāng)音相近的閩南就成了避難的首選。當(dāng)時還出現(xiàn)了這樣的婚嫁潮——有人從中牽線,,在閩南這邊提前找個夫家,,然后一大撥女孩像偷渡客一般,被人領(lǐng)過來,,再一一到對應(yīng)的夫家落戶安生,。這其實等同于集體自我販賣,。
祖母就是那時被人領(lǐng)過來的人潮中的一個女孩。當(dāng)時還發(fā)生了意外插曲,,原本說好的縣城那家男子,,不知是因祖母長得過于小巧,還是覺得她年齡偏大,,竟沒看上,。回,,一時半載是回不去了,,嫁,又沒嫁成,,祖母當(dāng)時竟成了尷尬的“剩女”,。幸虧,那同村祖父親戚家知悉情況后,,馬上介紹祖父與之相見,。當(dāng)時,我祖父也是大齡青年,,他的親事也愁壞了一幫親朋,。神話般,他們倆如同前世等來了今生,,竟一見傾心,。那一年祖父二十五歲,祖母也二十五歲,。
我無法想象祖母是這般潦草地嫁過來,,從此,家人杳無音信,,娘家又遠(yuǎn)在四百里外,,想回也是回不去的,何況那邊還戰(zhàn)火紛飛,,一個女人家到了舉目無親的異地,,和一個陌生男人成家,她是如何挨過那無邊無涯的漫漫長夜?除了相夫,、育兒,、持家外,還要面對眼前的戰(zhàn)亂,、饑荒還有動蕩,,可以說,祖母經(jīng)歷了中國近代百年最不平凡的歲月,,她是一粒飽經(jīng)苦難淘洗的沙子,,平淡無奇,,一生折射出來的卻是一部史書。
小時候,,我總是猜不透祖母的身世,。鄉(xiāng)下年節(jié)都要走親戚,我從不見祖母家的任何親戚上我們家來,,也未見我們家有誰上她娘家去,,她的身世對我是個謎。一度我真懷疑她沒有娘家,,甚至沒有娘親姐妹,,可能她就是祖父從路邊撿來的一個人。祖母很疼惜我,,一天到晚總是乖仔長乖仔短地掛在嘴邊。她夸我“乖”,,反讓我張不開嘴問她有關(guān)她娘家的一切事情,,一個沒有娘親的人多可憐,我真怕傷了她的心,。而祖母也從不和我說她的往事,。可能是她認(rèn)為我還小,,說不明白,,也可能她認(rèn)為還沒到說的時候。到我上學(xué)識字后,,再隨祖母去看戲,,便認(rèn)得“潮州”這地名。一聽,,祖母說的話和戲臺上那些人同音同腔,,我便明白祖母應(yīng)該是來自潮劇故鄉(xiāng)的那邊人。但我不敢說破,,我怕戲散場后祖母也被那幫“娘家人”領(lǐng)走了,。我常想象著她“娘家”的樣子,一定是戲里說的一樣,,亭臺連著樓閣,,楊柳堤,曉風(fēng)殘月般的模樣,。
大概是上四五年級的某天,,祖母把我叫到一旁,很慎重地對我說:“乖仔,,你大漢了,,書讀得好,,字也寫得比阿嬤卡水,以后給我阿姊寫信的任務(wù)就交給你了,。”祖母說我長大了,,字也比她漂亮,讓我代筆給她姐寫信,。那一刻,,我才真真切切知道祖母故鄉(xiāng)在哪里,并且知道她還有一個姐姐,。
阿姊,,見信好!最近你那邊一切可好?你和姊夫身體可安康?我這邊一切都好,不必掛念……
祖母用濃濃的潮音口述,,我一邊默默地記著,。信的內(nèi)容倒不新奇,千篇一律的問候,,除了訴說兩邊親人的近況外,,頂多再加些家常里短,都是再稀松平常不過的事,。姐妹倆你來我往,,書信成了連接祖母與故鄉(xiāng)的一根線,十幾年間從不間斷,。“潮州市潮安縣庵埠鎮(zhèn)竹排街陳賽琴收”這些字眼我已爛熟于心,,記不清寫了多少遍。直到祖母的姐姐去世后通信才漸漸停歇,。
從代筆那時起,,祖母和我說起老家的事就漸多起來。她阿爹是個商販,,經(jīng)營著一家很有規(guī)模的蜜餞店,,家里日子好得很。在當(dāng)?shù)嘏锒疾簧蠈W(xué),,她阿爹就生她姐妹倆,,她阿爹和阿娘視若明珠,姐妹倆都上了多年私塾,,讀過很多詩書,,還學(xué)了針線女紅,在當(dāng)?shù)睾苡写蠹议|秀的風(fēng)范,。
而一說起潮州的事,,祖母的眼睛總閃著亮光,仿佛早已穿梭在潮州的大街小巷上,甚至都聞到了那空氣中飄著腸粉和蜜餞的味道,。潮安縣庵埠鎮(zhèn)竹排街27號的那座老宅子,,就像戲臺上的布景似的,一下閃現(xiàn)在眼前,,還有阿爹阿娘那親切的笑臉在眼前晃個不停,。
“我老家那個戲臺是鄉(xiāng)社里最好式的,我們家深井(天井)的喇叭花開得真正水,,我阿娘做的腸粉,,真正好料,我阿爹做的蜜餞是我們那條街上最出名的,。伊倆人早早就走了,,我連最后一面也沒見到。唉,,這世人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這些話祖母不知對我念叨了多少遍,。我也是從她的話中得知,,潮汕淪陷時,,她姐已嫁,她為避免淪喪日軍魔爪,,才會踏上匆忙遠(yuǎn)嫁之路。而祖母的雙親早在上世紀(jì)解放初期就雙雙離開人世了,。后來親姐雖聯(lián)系上了,,但一連串社會運動和自然災(zāi)害,加上交通極不便,,讓她回潮州之路始終難以成行,。平和到潮州,那跨省際之間的交通,,一周也難有一趟班車,,而且還不是直達。要先從平和到漳州,,再從漳州到汕頭,,再從汕頭到潮州,一個來回上千里,。還要避開農(nóng)忙,,還要避開臺風(fēng)這些惡劣天氣,包括一家老小都健康平安時才敢出行,。這樣層層疊疊算下來,,走一趟親戚折騰三年五載都沒成行。改革開放后,交通日漸便利,,但祖母說她那把老骨頭經(jīng)不起折騰了,。遠(yuǎn)遠(yuǎn)聞到汽油味就吐得不行,何況乘車,,路況又差,,一路搖搖晃晃還要轉(zhuǎn)三四趟車一整天也未必能到潮州,這豈不要她老命,。好幾次人都走到車站了,,但一聞到那味道,頓時狂吐起來,,想想還是算了,,真的扛不住這趟長途之頓呀!到她離世,祖母竟一趟也沒回過潮州,。故鄉(xiāng),,成了她醒不過來的一場夢,像劇情一般,,長亭連著短亭,,卻一一飄向遠(yuǎn)方。
三
祖母常戴著老花鏡坐在門口讀書看報,,那情景是刻在我腦海中最美的畫面,。潮州人會過日子,善做蜜餞和小吃,。這些手藝祖母心底都扎了根,。桃子、李子,、楊梅,、橄欖、橘子皮,、西瓜皮……她都能變著花樣,,做出口味紛繁、令人垂涎的蜜餞,。自制蜜餞外,,祖母還會做服飾。我小時候穿和吃飯衫就是她做的,,可漂亮啦,,還鑲著漂亮木耳邊,胸前還別著一條她繡上花的小手帕,。這些原創(chuàng)的衣物引得小伙伴們眼饞,,我甚為得意。祖母善把平淡的日子過得精致有味,一絲不茍,。每次洗好我的白球鞋后,,她總要在鞋面上涂一層白白的香粉,還要貼上皺紋紙,,這樣曬干后,,黃漬就會被吸附在紙上,鞋子自然一塵不染,,白得耀眼,。從未發(fā)現(xiàn)全校哪個同學(xué)的鞋比我白。那時家里沒熨斗,,衣物皺了,,祖母就把它平整地放在床褥下,等褶皺消失了才拿出來穿,。上學(xué)時,,我也從未發(fā)現(xiàn)哪位同學(xué)穿戴比我整齊。不光把我收拾利索,,祖母自己也從不例外,。她身材嬌小,面容姣好,,最愛穿月白色的襯衫,,灰藍(lán)色的闊腿褲,素凈脫俗,,走路來衣袂飄飄,,步履生姿,天生一副書香風(fēng)韻,。她那“清湯掛面”式的中長發(fā),,兩邊發(fā)鬢用兩支銀色發(fā)夾別住,,每次梳頭都要抹上茶油,,梳得一絲不亂,偶爾還會在一邊簪上一兩朵玉蘭花,。那樣子,,總會讓我想起一棵開著花兒的老樹。
小時候我很不解,,愛美的祖母為何打扮得這么素凈,,后來那次我去潮州旅行時才發(fā)現(xiàn),很多潮州女子跟祖母穿著類似的襯衫和闊腿褲,,有些老太太的發(fā)髻上也插著玉蘭花,。剎那間頓悟,原來祖母“曲不離口”的潮音,就藏在那一朵朵玉蘭花的幽香里,。彳亍在古城蜿蜒的石板路上,,我強烈地感受到祖母的潮音無處不在。它在腸粉裊裊的熱氣里蒸騰,,在蜜餞的甜味里發(fā)酵,,在雕花的窗格里深嵌,在一磚一瓦里的紋理里鐫刻,,在老爺廟鼎盛的香火里繚繞……祖母跟我們說起的打上故鄉(xiāng)烙印的那些話語,、那些場景,頃刻間如韓江的波浪洶涌而來,。
祖母對自己一絲不茍,,對我也是。她最常對我說“過日子一點都不能潦草”,。她說女孩子要有坐相體態(tài),,待人接物要有方寸,衣著要干凈大方,,頂頂要緊的是要認(rèn)真讀書,,不能只當(dāng)一朵花兒,要有挺立的枝骨,,就像戲里的大小姐那般,,一言一行都透著大家閨秀的模樣。她這些話猶如家規(guī),,從小就不斷地鞭策著我,。
祖母漂亮聰慧,有才情,,又有文化,,心氣也頗高,她不愿到街頭巷尾去嚼舌,,寧愿自己靜在一旁也絕不扎堆,,很少見她有朋友往來。她最常常念叨的還是記憶里的潮州,,“今天是我們潮州‘營老爺’的日子,。”“我們潮州的廣濟橋是全國有名的,非常水,。”“我們潮州的燒火龍,、弄花燈、燒瓦窯,,非常熱鬧,,非常好看,。”只要把記憶中的潮州大閘拉開,即使只有我這一個小聽眾,,她也能滔滔不絕地說上大半天,。看我似懂非懂的樣子,,她總會長嘆一聲——唉!這一聲“唉”讓我感覺像一口深井里傳來的回音,,寂寥而久遠(yuǎn)。接下來祖孫倆會陷入相顧無言境地,,但很快她或我便會先行走開一會兒,,往往此時,我便會聽到一支柔柔曲調(diào),,又是祖母在清唱她的潮劇,。
四
《四郎探母》是潮劇經(jīng)典劇目之一,每年都會上演,,祖母早于熟爛于心,。而這樣的大戲一開鑼,她便如魂附體般貼著臺上的每一個節(jié)奏哼唱起來,,如癡如狂,。
“我有心過營去探母,怎奈我在番邦隔天涯,。想老娘不由我肝腸寸斷,。眼睜睜高堂老母難相見,兒的娘要相逢,,除非是夢里團圓……不,、不,到了,、到了!”
劇情一到高潮處,,未吟淚先流,臺下的祖母早已青衫濕透,??吹剿@般情景,我經(jīng)常嚇得連話都不敢說了,,更別說糾纏她要錢買零食,。我甚為不解的是,,劇情并不復(fù)雜的楊四郎探母,,為何每每讓祖母如此動情。劇情里身為遼國駙馬的楊四郎,,為見母親,,冒著生命危險拿到令箭,,歷盡艱辛回家。我當(dāng)時猜想,,戲臺上的楊四郎,,任何一個疏忽都是致命的,他難道不怕掉腦袋嗎?難道他不能等到掌了實權(quán),,手握令箭的那天嗎?這樣豈不更穩(wěn)妥些?他真傻!聽了我的疑問,,祖母摸了摸我的頭說:“傻囡仔,等你長大離開家就明白了,。”
上幼兒園那年,,祖父買了臺錄音機,這在當(dāng)時可是比較罕見的奢侈品,。它可以收音,、播放磁帶、錄音,,在我們這里也被俗稱為“三用機”,。有了三用機,家里就成了大戲院了,,咿咿呀呀的聲音不絕于耳,。祖母魂兒都被三用機勾走了,特別是播到她心儀的唱段,,仿佛機子里的演員頃刻就附體在她身上,,合二為一了。只見她嗓子一亮,,蘭花指一翹,,眉毛一挑,腰肢一扭,,蓮步生風(fēng),,踏起層層波,枯瘦的身板輕巧靈動,,竟有著少女般的韻致,。唱到激動處,掃地時的掃把,、吃飯時的筷子,、炒菜時的鍋鏟無一不成為她打節(jié)奏的器具。她那如癡似醉,,近乎癲狂的樣子,,總是惹得我忍俊不禁。
祖母音域極廣,,唱得了花旦,,也能唱小生,。《四郎探母》的楊四郎經(jīng)典唱段是她的摯愛,。
“想當(dāng)年好不黯然,,我好比那籠中鳥,有翼難飛展;我好比那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那南飛雁,,失群紛飛散……”
祖母跟著三用機掏心掏肺地唱著,飽經(jīng)風(fēng)霜的嗓音,,醇厚蒼勁,。那凄涼的曲調(diào)一字一句地從口中唱出來,心里的苦也便一點點倒了出來,。她時而踱著虎虎生風(fēng)的方步,,時而雙手輕顫,枯瘦的身影也仿佛一下子蒼老了許多,。此時的她覺得自己就是一只孤單失群的大雁,,正竭力地扇動著翅膀,飛過了花山溪,,飛過柏嵩關(guān),、飛過三河壩、再飛過了韓江,,近了,,近了……可故鄉(xiāng)卻是眼前的海市蜃樓,任憑她怎樣用力撲騰翅膀,,怎樣拼命呼喊,,總是近似咫尺,卻仍在天涯,。
“我有心過營去探母,,怎奈我在番邦隔天涯。想老娘不由我肝腸寸斷,。眼睜睜高堂老母難相見,,兒的娘要相逢,除非是夢里團圓……”
戲到高潮處,,祖母已淚眼迷離,,雙手輕顫,那清亮的聲音一下子變得低沉粗澀,,仿若寒冬的溪流在凍結(jié)的堅冰下艱難地涌動,,又恰似一把刀割裂了錦帛,再探入心里,,一刀一刀地把整個人都掏空了,。不,此時的祖母,,不再是一只失群的雁鳥,,她分明是一只啼血的杜鵑。在戲里她肆無忌憚,、聲嘶力竭地呼喊,、流淚,我已分不清是她演繹了千年前的楊四郎,,還是楊四郎演繹了今世的她,,仿佛隔著三用機那層薄薄的鐵殼子,他們倆可以自由穿越,,互換角色,。
那臺三用機用到我?guī)煼懂厴I(yè)參加工作了都還沒壞,它竟比祖母的身子板還結(jié)實,。就在我臨近師范畢業(yè)的前幾個月,,祖母身體出現(xiàn)了異樣——吃飯總會被嗆著。父親帶她去醫(yī)院檢查,,結(jié)果是食道癌晚期,。家里人對我隱瞞了這個結(jié)果,他們擔(dān)心我接受不了這個現(xiàn)實,。
在我上班的第一晚,,祖母走了。我的淚像屋檐水般砸落在地上,。
“我有心過營去探母,,怎奈我在番邦隔天涯。想老娘不由我肝腸寸斷,。眼睜睜高堂老母難相見,,兒的娘要相逢,除非是夢里團圓……”
多少年過去了,,只要《四郎探母》的潮音一響,,我頓時就會被定住一樣,再也難以挪步,。循著這熟悉的聲音,,那顫巍巍的身影又仿佛在眼前晃動??偸锹犞犞?,那不爭氣的淚水又流下來了,從那渾圓的唱腔里,,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楊四郎就是祖母,。雖然,祖母從二十五歲離家到七十七歲離世,,最終沒有再踏上故土一步,。但她始終相信有回家的一天。祖母是在借楊四郎回家,,借著潮音讓她翻過千山萬水,,回到她魂牽夢繞的——潮州市潮安縣庵埠鎮(zhèn)竹排街。無論是在劇中,,還是在夢里,,潮音成了她回鄉(xiāng)的羽衣。
原刊責(zé)任編輯:林東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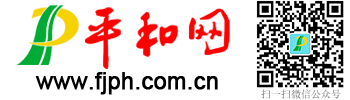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