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拔兔草
我的童年是在物資匱乏的八十年代度過的,,在吃飽肚子尚且需要奮斗的年代,,相片自然是很少拍的。但有什么關(guān)系呢?在歲月的長河里,,童年像一首清澈的歌,,一直在耳旁回蕩、在心底回響,。那些美好的童年往事,,化作永不褪色的相片保存在記憶的芯片中。
我讀小學(xué)的時候,下午四點十分就放學(xué),。放學(xué)后,,我常和伙伴們到田野里去拔草喂兔子。拔兔草,,可以理解為家長布置的一道“作業(yè)”,,但這道作業(yè)卻很受歡迎。因為田埂上,、菜畦旁,,漫天都是野草。我們這群女娃只要依據(jù)長久以來積累的經(jīng)驗,,不用費太多功夫便可以完成任務(wù),。剩下的時間里,我們是自由的,。只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家就可以,。依照慣例,我們可以在田野上盡情地玩耍,。---“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們之意不在免草也。
陽光從西邊的山頭斜照在田野上,,廣闊的田野和起伏的群山,,都美成了一幅油畫。拔完兔草的我們穿梭在田野間,,找尋如精靈般散落的小野花,。夕陽下、晚風(fēng)里,,她們輕輕搖曳,,似乎在招引我們這群愛美的小姑娘們前來與她相會。梅把摘下的野花插在發(fā)梢上,,芬把野花別在耳廓后,,而我索性做一個大花環(huán),戴在脖子上,。綠綠的田野,,溫暖的夕陽,花仙子一般的小姑娘,,這不是童話里才有的場景么?
花摘多了不好拿,伙伴們各出奇招:有的就地取材,,找根藤條把花兒扎成一束;有的摘完花還不盡興,,還自制了花瓶。田里都是泥,找些干濕合適的黏土,,化身制陶大師,。或捏或拉,,或壓或擠,,一個粗線條的土味花瓶就做好了。把各色野花往“花瓶”里一插,,竟也十分和諧,,野味十足。我曾為了這么一個花瓶,,把自己活生生變成個小泥人:額頭,、兩頰、甚至睫毛上都粘上了泥,,胸前的衣服也早已一片土色,。好不容易做成了,便捧著自己的“得意之作”往回跑,,全然忘了自己是來拔免草的,,身后伙伴們早已笑得前仰后合。
那個“土”味十足的花瓶,,那些野味十足的花兒被我放在窗臺上,,陪我晨起讀書,陪我晚間睡眠,。風(fēng)吹著,,太陽曬著,不幾天它們就成了干花,,擁有另一番別樣的韻味,。在那個缺少美的童年時代,它們美了我和伙伴們的窗臺和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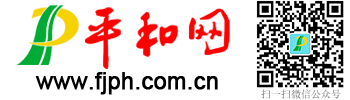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