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荔枝紅了
漳州是有名的花果之鄉(xiāng),,這“果”里肯定是少不了荔枝的。記得有一年去西安旅游,,當(dāng)?shù)厝艘宦犝f我們是漳州人,,羨慕不已,都說:“漳州人真有口福,,你們那里的荔枝太好吃了!”說這些話的時(shí)候,,他們是兩眼放光,一副垂涎欲滴的表情,。“一騎紅塵妃子笑”,,大抵楊貴妃見到荔枝時(shí),亦是這樣的表情吧。不要說是外地人,,我們本地人對(duì)荔枝也是情有獨(dú)鐘,,百吃不膩。
鄉(xiāng)下老家的屋后有一棵老荔枝樹,,相傳是曾祖父的父親種的,,是我最愛吃的白蜜荔枝。
家鄉(xiāng)的荔枝品種最常見的有黑葉和白蜜兩種,。黑葉,,葉子顏色比較暗,呈墨綠色,。這個(gè)品種的荔枝產(chǎn)量高,,甜度也很高,缺點(diǎn)就是核比較大,。白蜜相對(duì)黑葉來說,,產(chǎn)量比較低,甜味沒那么濃,,是一種獨(dú)特的,、淡淡的清甜,果核很小,,果肉飽滿,,綿軟多汁,口感極佳,,很合我的口味,。
小時(shí)候最快樂的事莫過于跟著老爸去采荔枝。老爸是爬樹高手,,身手敏捷地在高大的荔枝樹上穿梭,,很快紅彤彤的荔枝就裝滿了一個(gè)個(gè)竹籃。我負(fù)責(zé)把多余的枝葉擇去,,還有撿起散落在地上不成串的荔枝,,顆粒歸倉。采好荔枝,,我們便開始坐在樹下大快朵頤。老爸總能準(zhǔn)確無誤地挑出一些近乎無核的荔枝來,,而這些“極品”又總歸我一人專享,。鮮美的汁水在口齒間奔涌不息,甜透了心窩,,就連周圍的空氣都是甜絲絲的……
吃剩下的荔枝核可以拿來做陀螺,,這也是老爸小時(shí)候常玩的游戲。老爸是個(gè)急性子,但陪我玩卻很有耐心,。他用小刀切掉荔枝核底部大約三分之一的長(zhǎng)度,,留下尖頭的那一端,拿出一根牙簽折掉一段,,把它插在切口橫截面正中,,這樣一個(gè)小巧玲瓏的陀螺就做成了。把陀螺的尖頭朝下,,牙簽朝上,,立在平整的地面或桌上,人手一個(gè),,捏住牙簽,,同時(shí)順手用勁一捻,一場(chǎng)轉(zhuǎn)陀螺比賽就開始了,??凑l轉(zhuǎn)的時(shí)間長(zhǎng),誰就贏,。輸?shù)娜艘悔A的人用手指刮三下鼻子,。老爸每每看到我輸了多次,那個(gè)跟他長(zhǎng)得一模一樣的鼻子被刮得通紅時(shí),,總會(huì)于心不忍,,故意輸給我,而我總會(huì)毫不客氣地對(duì)那個(gè)帥帥的大鼻子下了手,,他也總會(huì)故作夸張地哇哇大叫,,向我求饒,那狼狽樣惹得我忍俊不禁,。
童年初夏的風(fēng)里,,到處飄蕩著荔枝味兒的歡笑聲……
后來家搬到了縣城,就沒有再跟老爸去摘過荔枝了,??赡苁翘贸粤说木壒剩笾μ貏e招蟲子,,蛀果蟲總愛鉆進(jìn)蒂頭處蛀食果實(shí),。因此,每年荔枝掛果時(shí),,就是果農(nóng)最忙的時(shí)節(jié),,噴蟲保果,幾乎隔幾天就要噴一次,。老爸為了讓我吃上自家那上好的白蜜荔枝,,每年五六月份期間,,都要多次驅(qū)車到幾十公里外的老家去給那棵老荔枝樹噴蟲。老媽總是嗔怪他:“要吃白蜜荔枝還不容易,,那么多趟的車油錢和勞工費(fèi)湊起來,,夠在市場(chǎng)上買來吃個(gè)痛快了,何必那么辛苦!”他總是笑嘻嘻地反駁:“還是自己家種的比較放心,,比較好吃,,誰叫我家丫頭就好這一口呢!”
如今,省城的水果店早早就擺上了來自外地早熟反季的荔枝,,鮮紅嫩綠的,,甚是惹眼。但總覺得那不是家鄉(xiāng)的味道,,沒有想吃的欲望,。只是一到夜深人靜的時(shí)候,便撓心撓胃地想念起了老家那棵老荔枝樹上掛著的一串串美味,。
不知道是不是心靈感應(yīng),,沒過幾天,手機(jī)上收到老爸的一條信息:跟我們家的吃貨報(bào)告?zhèn)€好消息,,今年老家的荔枝樹掛果特別多,,已經(jīng)快成熟了,過陣子等荔枝紅了,,給你和宿舍的同學(xué)寄幾箱過去,,解解饞。
恍惚間,,透過手機(jī)的屏幕,,眼前出現(xiàn)了一幅幅畫面:那個(gè)高大壯實(shí)的身影又在枝繁葉茂的荔枝樹上晃啊晃;那個(gè)扎著兩條羊角辮的小姑娘又提著籃子,踮著腳在荔枝樹下抬頭望啊望;那個(gè)荔枝核陀螺又在地上滴溜溜地轉(zhuǎn)啊轉(zhuǎn),,仿佛永遠(yuǎn)不會(huì)停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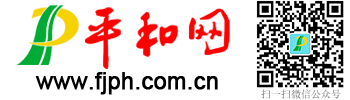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