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塘記憶

福塘村能夠走進記憶,,是因為1990年從師范畢業(yè)分配到秀峰小學(xué)任教的機緣。報到那天,,恰逢雨后公路塌方,唯一的班車停開,,四個新分配的師范生徒步18公里,,前往秀峰小學(xué)。咬牙緊撐,,到了福塘村,,聽說還要三公里,就像練武術(shù)的人撐著的一口真氣泄了,,頓時,,無助、疲勞等侵襲而來,,福塘村成為一個傷悲的注腳,。習(xí)慣之后,在后來的日子,,每每走到福塘村,,返家的時候,離家近了三公里,還有十五公里;返校的時候,,則是離家十五公里,,還有三公里。無論距離的遠近,,福塘村都成為一個參照物,,楔在心頭。
福塘村舊稱上大峰,,秀峰一度被稱為小峰,,一大一小和其他幾個地名成為佳聯(lián)“上坪下坪赤草埔,大峰小峰白花洋”,。這里和九峰,、永定、崎嶺等等相通,,不過,,在我的記憶之中,福塘的滋味一言難盡,。當(dāng)年在秀峰小學(xué)任教的時候,,交通不便,閉塞,、寂寞,、孤獨、無所事事成為我和在福塘小學(xué)任教的林弋兩個人共同的標(biāo)簽,。放學(xué)的時候,,我拎著一瓶綿竹酒和一包魚皮花生,從秀峰往福塘走,,林弋則是從福塘往秀峰走,。到了半路,我們相逢,,就在路旁的草地坐下,,喝一口酒,往嘴里丟一顆魚皮花生,,漫無邊際地閑聊,。有風(fēng)吹過,山里的公路靜寂無人,,也沒有車輛,,土路旁的塵土飛揚,茅草衰黃,,荒涼的感覺順酒氣而上,,酒喝完了,把空酒瓶扔到路下的小河,沒有什么聲響,。我和林弋分手,,默默地行走,偶爾回頭,,會看到暮色落在對方的后背,蕭殺,、蒼涼,。福塘的村道上,也就不時承載了我們青春的淚水,。

在村里,,我和林弋時常到圩場一個叫阿堆的椿臼面面店吃面。椿臼面是福塘的特色小吃,,自種的小麥磨成粉,,和面不僅僅是在面盆里,而是放到石臼椿,,翻來覆去,,把面團椿活了,然后上板,,用一把很大的刀切成面條,,比正常的面條粗,而且和機制的面條是圓形的不同,,椿臼面是方形的,。椿臼面比普通的面條煮的時間要長,撈到碗里,,不粘不散不爛,,澆上香油,加上用大骨熬成的湯,,放幾簇自家種的空心菜或者韭菜,,吃起來有嚼勁,筋道足,,足以讓人體會到風(fēng)卷殘云,。阿堆的椿臼面從開始的每碗三毛錢到現(xiàn)在的每碗五塊錢,經(jīng)歷了二十多年的時間,,至于椿臼面上了央視《遠方的家》,,那是去年才有的事情。椿臼面留給我的還是當(dāng)年和林弋一起吃面的情形,,我們時常是一碗面條一碗扁食混合在一起成為一大碗,,每個人兩大碗,然后切一點豬頭皮,闊綽的時候,,上兩瓶綿竹酒,,把日子吃得稀里嘩啦。
吃過面條,,我們喜歡無所事事地在福塘村里穿梭,。我們跑到在塘背科的“聚奎樓”,這座土樓有三層高,,以八卦形設(shè)計,,樓里門窗都有石雕楹聯(lián)字畫,楹聯(lián)詩文清新簡潔,,如“瞻高望遠:瞻高邀明月,,望遠看奇花”、“仰觀俯察:仰觀對月飲,,俯察思祿永,。”“清風(fēng)徐來好,明月桂花香,。”“夕陽紅半樓,,遠水碧千里”等等,門窗的縫隙里就傳出書香的雅韻,。始建于清乾隆年間的“南陽樓”也留下我們的足跡,,據(jù)說這座樓是朱熹的18代子孫朱宜伯設(shè)計督建,當(dāng)時是蘑菇形狀,,裝修十分別致,,只是這僅僅是村人口中的描述,南陽樓只剩下石柱子,。更喜歡的是在河邊坐下,,聽河水淙淙流走,偶爾扔一塊小石子,,發(fā)出撲通一聲響,。或者丟向在屋檐下休憩的雞群,,把雞群嚇得一驚一乍,。或者,,穿行在小巷里,,體驗?zāi)欠萸鍥觯灰敢?,在哪家的石門坎坐下,,恍惚回到童年,。“壽山聳秀”樓、觀瀾軒,、留秀樓,、茂桂園樓等等故事不少,在哪里坐下,,或許就是坐在一段歷史之上,,隨便在小巷里拍拍墻壁,說不定就驚醒些許歷史風(fēng)云,,而“桂巖書院”,,“文峰齋”書館的書香,不經(jīng)意間就在村里飄蕩,。
周末的時光,喜歡和林弋一起去爬山,。福塘村和秀峰村連接的古道,,時常留下我們的身影。古道連接秀峰和福塘兩個村莊,,從兩個村莊近似直線距離的地方翻越山頭而成,,蜿蜒曲折,成了當(dāng)時的交通要道,。那地方原來只是一條從茅草叢中踏出來的小路,,鄉(xiāng)下到處可以看到的小路一般,人往來,,各種牲畜也經(jīng)過,,沒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古道有了歷史的味道是因為明朝時秀峰村的游百萬,,這個從秀峰村走出去的從販賣煙葉開始的生意人,,因為聰慧和機緣湊巧,發(fā)財了,。發(fā)財?shù)挠伟偃f有了光宗耀祖的念頭,,就回秀峰村建了深庭大院,為了顯示財大氣粗的顯赫,,建造房子的石柱子是從當(dāng)時的龍溪府購買而來,,當(dāng)時可沒有船載車運,這些石柱子是用人工抬送到秀峰村的,。曾經(jīng)到游百萬那豪宅尋探,,只殘余下幾段石柱子,其他房子的蹤跡了然無痕了,。殘余的石柱子寂寞地豎立在那里,,成了哪家栓牛羊的工具了,。
當(dāng)年為了抬送石柱子,游百萬修了這條道路,,也許是為了方便,,也許出于公益事業(yè)心理,也許還是財大氣粗的豪氣,,游百萬在這條道路上全部鋪上了條石,,那時候,條石鋪就的道路可和如今鋪上水泥路面的道路一樣,,有著闊綽的舒適,。路面不寬,也就兩個人并排行走的寬度,,可以想象當(dāng)年十來個人抬著石柱子在這條道路上行走,,還得稍微前后錯身,把汗水和指揮節(jié)奏的號子聲留在沿途的條石上,。在山頂上,,還修建了一個涼亭,小小的,,但足以行路人在這里歇息片刻,,有風(fēng)雨的時刻,還可以在涼亭下看風(fēng)雨被拒于幾步之外,,感受到免于風(fēng)雨之苦的暖意,。相信當(dāng)時對游百萬的贊譽之辭如山風(fēng)一樣隨處飄蕩。
站在山頂?shù)墓诺郎?,可以清晰地看到兩個村莊,。田野里蓬勃生長的莊稼,炊煙裊裊的村莊,,勞作的農(nóng)人,,行走奔跑的牲畜無不在視線之內(nèi)。古道時而清晰地出現(xiàn),,時而隱沒進道路兩旁旺盛葳蕤的茅草之中,,穿行在云層中的游龍一般。至于福塘村以太極村聞名,,那是近幾年的事情,。據(jù)說站在山頂之上,可以看到一泓溪水成S形狀流入村中,,正好是一條陰陽魚的界限,,將村莊南北分割成“太極兩儀”,而溪北聚奎樓,、溪南南陽樓分別位于“陰魚”和“陽魚”的魚眼處,,全村很像一個道家的陰陽太極圖,,太極村因此成名。
和林弋很久沒有去爬福塘的山了,,林弋在廣州,,城市喧囂,他或許也很少想起福塘的椿臼面了,,福塘村在我們的記憶日漸模糊,。曾利用周末時間特意跑到福塘村的阿堆椿臼面店,老板還是阿堆,,店還是在那里,,至少稍微擴大一點點,阿堆不再是年輕的小伙子了,,當(dāng)年很熟絡(luò)的人如今已是陌生,。看到阿堆提著一籃剛從地里采摘的空心菜進來,,正要打招呼,,他又走出去了。在他的眼中,,我僅僅是一個吃面的人。歲月會抹去許多東西,,即使是秀峰的古道也是湮沒在雜草之中了,,只留下若隱若現(xiàn)的痕跡。偶爾才會被人在茶余飯后閑聊時提起,,也許很快就沒有人再提起了,,古道也就完全退隱出生活之外。
而福塘村,,終將成為我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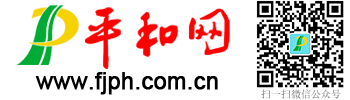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