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元宵月
暮色中,,蒼山如大海遼闊。從縣城一路往西,,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浪濤翻涌,,班車像一葉扁舟在浪尖上行走,左一下,,右一下,,東搖西擺,騰云駕霧一般,。
從年初四,,整整十一個日夜,陪著父親從鄉(xiāng)下到縣城,,再到漳州175醫(yī)院,,和病魔展開一場前途未卜的競賽,。醫(yī)院長長的甬道里,,隨處是恓惶的身影,以及隱忍的表情,,在白白的燈光下,,生命變得如此不靠譜,一點點地虛幻起來,。一向高大的父親在我面前一節(jié)節(jié)變矮,、變小,在醫(yī)院的迷宮中倉惶四顧,,唯有身邊的兒子成了唯一可依附的生命稻草,,他如嬰兒般緊緊跟隨,只差拽著我的衣袖,。而我卻被大夫指揮得團團轉(zhuǎn),,無暇他顧。此時,,父親的老命就拽在我手上那一沓檢查單里,,像剛拋出的卜卦,在空中劃出一道未解的弧線,。
實在太困了,,我竟在顛簸中鼾聲驟起。父親如那盞搖曳的油燈,,一會遠,、一會近,很快就晃到半年前的故鄉(xiāng)橋頭,,父親挑著煤,,扁擔彎成下弦月,,如一幅夸張的油畫,黝黑的后背筋骨畢露,,像一張滿弓的弦,,佝著背艱難向前邁步,額頭汗如雨下,。就在個把鐘頭前,,我剛和她分手,我在探親中途草草結(jié)束了一樁陳年的愛情,。那時,,我沒有一滴淚水,頭也不回地吹著口哨離開,,把她拋在初見的山坡上,。眼前的父親,卻在一瞬間把我從恍惚的云端拽到堅硬的地面,。突然有塊東西梗在喉結(jié),,我吐不出來,也咽不下去,,我扔下背包,,跨步上前奪過他肩上的扁擔,飛快向前沖去,,生怕身后的父親看見我模糊的臉龐,。
突然,一聲刺耳的尖叫伴隨一串瘆牙的機械制動摩擦聲,,夢境中的父親跌跌撞撞地向濃霧中隱去,。我重重地磕在前排靠背上,一睜眼,,一車惶恐的神色,。司機掀開引擎蓋,左敲右打地忙乎一陣子,,終于站起來朝大家一攤手,,說:“油泵壞了。”他以一個無奈的表情告訴大家,,我們被拋錨在一個叫草嶺的山腰上,。
離家還有百多里地,暮色已從山腳漸漸圍了上來,,最后一縷余暉早已沒在山頭的林梢里,。在這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半坡上,焦慮寫在每個人臉上,。一車人三三兩兩散開了,,只留下司機和售票員兩人守在原地,。大家四處張望,都盼著要是能來輛順路車就好了,。這時,,我聽到遠處傳來鞭炮聲,已經(jīng)入夜了,,山腳下的村莊開始鬧元宵了,。
這時,山腳下竟轉(zhuǎn)出一輛中巴車來,,大家齊齊轉(zhuǎn)身,,死死地盯著那輛甲殼蟲般的中巴車,左搖右晃,,很吃力地一步步向前爬來,。越來越近,終于看清了,,原來是因故而耽擱前往隔壁鄉(xiāng)長樂的班車,。到了長樂再雇摩的回家不會耽擱太多功夫。大家一塊奔向路中央揮手攔車,,中巴車仿佛受了驚嚇,,打了幾個趔趄才停了下來,,大家蜂擁而上,。就在我也要擠上車時,這時售票員叫了我和其他幾位鄉(xiāng)親的名字,,我猶豫了一下,,就從車上擠了下來。
售票員其實是車主,,他還是我小學的同桌,。這荒山野嶺的,就他和司機留下來確實讓人操心,,何況這叫大協(xié)關(guān)的地方歷來是匪寇出沒之地,,前陣子還鬧過搶劫的事。最終,,我和六位鄉(xiāng)親留下來,,包括我的堂弟。
好在司機沒有放棄,,他拿出工具箱趴在引擎上忙個不停,。這個從部隊汽車連回來的老司機,忙乎了一個多鐘頭,,奇跡出現(xiàn)了,,引擎被他重新發(fā)動起來,,大家都松了一口氣。這時,,司機卻說,,六缸的動機只有兩缸在工作,能否順利到家憑運氣,,剛放下的心又懸了起來,。車子爬得非常緩慢,畢竟,,它受了嚴重內(nèi)傷,,只有三成功力在苦苦支撐,何況又是陡坡,,我真替它擔心,。果然,過了大協(xié)關(guān),,班車就徹底拋錨在一個叫五斗的地方,。只能就地待援,等待縣城的師傅前來換油泵,。但相比草嶺,,我們畢竟到了一個村莊,到了一個不再提心吊膽的地方,。
路邊那一排紅燈籠像是在善意的提醒我,,此時,鄉(xiāng)下的老母親,,也一定守在門前那盞紅燈籠下張望,,甚至,八副碗筷還都齊齊擺在飯桌上,。這是我們家的慣例,,過年過節(jié),父母總會把一家人的碗筷擺齊,,大哥一家四口,,連同我和弟弟,還有爸媽,,一個都不會少,。今年,弟弟沒討到薪酬,,他沒回家,。知道父親去醫(yī)院需要花很多錢,大哥一家人年初四就急著回廣東提前開張生意,。如今,,父親在醫(yī)院,,我陷在途中,我不敢回想離家前,,母親那欲言又止的神情,。
“看,快看,,月光出來了!”不知是誰一聲驚呼!大家尋著聲音齊齊朝山頭望去,,此刻,連一絲云彩都沒有,,夜空藍得出奇,,仿佛,此刻有另一個蔚藍的洋面倒掛在天上,。一輪圓月出奇的白,,出奇的亮。月光下,,大協(xié)關(guān)那條山路亮得發(fā)白,,宛如一條彎來繞去的銀河,很寫意地掛在山坡上,。
而我總覺得每條山路都是人間的哀腸,,每一步都浸透著辛酸的汗水。十六歲的父親,,肩挑百斤重擔往返于這條山路上,。拂曉出發(fā),黑夜歸來,,從秀峰坪洄到縣城,,一來一回二百多里地,,剛好可以換回五斤白米,。父親早逝,體弱的母親和幾個年幼的弟弟,,全靠父親肩上一根扁擔活命,。那時的父親像一架停不下來的轱轆,不管生活的那口井有多深,,他必需一頭扎進生活的井底,,任轱轆發(fā)出咿咿呀呀的聲響,從苦難的最深處撈起一家人的生活,。
汽車仿佛壓縮了時間的長度,,我們很難體驗旅途的距離。路,,只有用雙腳丈量才知道它的真實的分量,。橫亙在眼前的大協(xié)關(guān),,在父親的挑擔時還沒有公路,從老家坪洄到縣城小溪只有一條石階砌成的小路,,那是汽車誕生前就留下的驛道,。我見過挑山工,全身肌肉緊繃,,感覺有一股力從大地深處反彈起來,,從腳尖到腳跟,再到膝,、到髖,、到腰、到肩上,,仿佛,,全身上下每一個細胞都被鉸成一股繩,緊緊繃在那副重擔上,。在光滑的石階上,,每一步,都曾留下父親滾燙的汗水,。在漫長的攀登中,,肩上的擔子前搖后擺,那時的父親多像一棵樹呀!枝條橫擺,,枝桿卻必需挺直,,以山峰的姿勢越過每一道溝坎。年少的父親,,生活的全部就是每天的攀登與翻越,,每一步都幾近掙扎,這絕不是艱辛二字所能衡量,。借助皎潔的月光,,回望大協(xié)關(guān)嶺,才感受到,,當年它在父親的腳下,,每一步都那么沉重,莊嚴,,甚至神圣,。
父親曾說,他的肩上挑起了兩個家庭,,一個是他和母親及弟弟們,,另一個是我們兄弟姐妹五個。他肩上的那根扁擔,壓得越重,,垂得越彎,,而他的步子卻愈加堅定,父親是一位出色的擔山漢子,。如今,,日子漸有起色,年過花甲的父親卻病倒了,,只剩下一個病歪歪的軀殼,。此時,他陷落在醫(yī)院的病房中,。
這輪元宵月如云帆般一節(jié)節(jié)升起來了,,不知何時它已高高懸掛在夜空中。此時已是晚上九點半,,從縣城趕來的師傅已修好油泵,,我慶幸著,如果順利,,在子夜前就能趕到家中,。深夜的風有些涼,我感覺有雙翅膀在滑翔,。天上那輪圓月仿佛在和我們賽跑,,它就在車窗外,我走它也走,。我伸出雙手,,捧著這輪滿月飛快穿過兩旁的樹梢,一路向西,,穿過一座座山巒,,穿過合溪、穿過詩坡,、穿過礎溪,、穿過九峰,仿佛穿梭在時空的隧道中,。今晚的月光曾照在當年奶奶的窗前,,也照在母親無法入眠的床前,它一定看見當年父親餓昏昏,、叉著腰,踏著銀白的月色一步步往家趕的情境,。這蒼白的月光,,見證當年父親疲憊的腳步,也見證母親那不安的神情。
就在我胡思亂想中,,很快就到了長樂,。像是上蒼要考驗我,車子好像被什么顛了一下,,又熄火了,。此時,已臨近子夜,,鄉(xiāng)村早已沉浸在睡夢中,,路上連個人影都沒有,離家卻還有二三十里地,。走回家少說也要兩三個鐘頭,,留下來等?可是要等到什么時候。我可不能再等了,,這沒有答案的等待我等不起,,我朝堂弟打了一個手勢說:“走!”
堂弟卻勸我留下來等,同桌以及師傅和幾位鄉(xiāng)親都勸我留下來等,,都大半夜了,,急什么呢?而我卻不能再等了,我的包里還捂著一封“火速歸隊”的電報,。圓月當空,,我分明覺得有雙眼睛在天上看著我,我必需走,,說什么也不能讓母親一人熬過這個元宵夜,,我必需在今晚趕到家中,然后和母親告?zhèn)€別,,天明后背上行囊再次上路,,我不能陷在途中。我沒有回頭,,獨自一人上路,。很快,身后就傳來急切的腳步聲,,我知道那一定是堂弟,。我們誰也不說話,像在比賽,,大步流星地往家趕,。我們趕到秀峰橋子頭時,聽到身后一聲喇叭,,這一路故障不停的班車終于追上來了,。
等我趕到家中,早已過了子夜。我推開家門那一刻,,我看見母親一人坐在廳堂等我,,桌上八副碗筷整整齊齊一動也沒動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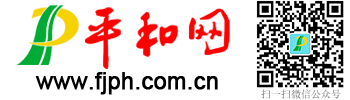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