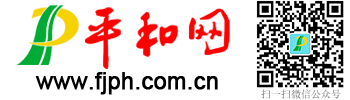親愛的五叔
那次回鄉(xiāng)下,,一到家母親便提醒我該去看望五叔,,五叔他還住在我童年的那個村莊里,那是一個更加偏僻的小山村,。五叔病很久了,,理應(yīng)去看他。過去這里也是母親的村莊,,她的戶口沒遷回故居,,還留在這個村。以前這個只有十余戶人家的小山村景色極美,,村后一片梯田,,村前一灣小河,依山傍水,,良田大片,。當(dāng)時有首童謠說我們村莊是:村后自來水,村前自來柴(發(fā)大水時撿大水柴),,有吃不發(fā)愁,。讓這個村莊更加有名的是我們村會養(yǎng)人,當(dāng)官的多,,美女也多,。那時,村莊雖不通大路,,但一年四季人來人往,,很是熱鬧。
一條新修的水泥路直通村莊?,F(xiàn)在幾乎所有的村莊都通大路了,,只是大路通暢了,,路上行人卻少了,再也見不到童年小路上那三三兩兩的行人,,大路冷冷清清,。偶爾遇上幾輛卡車,拉著滿滿的木材往城鎮(zhèn)的木材加工廠去,。條條大路使村莊不再閉塞,成為連接外部世界大通道,,連接城市與農(nóng)村,。一個個村莊就是城市的神經(jīng)末梢,既接收城市中樞輸送來的現(xiàn)代工業(yè)生產(chǎn)的化肥,、農(nóng)藥,,乃至鍋碗瓢盆一切生活所需,也包括那些孩子愛吃的膨化食品,,甚至城里積壓下來的垃圾產(chǎn)品,,農(nóng)村是清理垃圾的最好戰(zhàn)場,像是吸上了城里的鴉片,,成了永遠(yuǎn)的癮,。
當(dāng)然,一個個村莊又是輸送原材料的來源基地,,糧食,、木材甚至最廉價的泥土,運到城里甚至出口,,就成了寶貴的資源,。經(jīng)過冶煉、加工,,最后魔術(shù)般地變成飛機(jī),、大炮、汽車,、巧克力,、餅干、鍋,、碗,、瓢、盆……變成高價的商品,,一部分又源源不斷地流回村莊,,說不定你家的那口高壓鍋就來自后山上那眼礦石,也難說餐桌那包榨菜不是來自我家的菜園,。但它們已是商品,,每一件都戳著城里的商標(biāo)和印記,。靜下心來一想,通暢的背后是掠奪,,城市通過這些交通網(wǎng)絡(luò),,順暢地把手伸到了農(nóng)村。
路過白馬石,、寨子這些鄰村的大片良田,,這里集中兩個基點村上千畝的耕地,這些都是當(dāng)年農(nóng)業(yè)學(xué)大寨時平整過的基本良田,,這些良田很多都不種糧食了,,有的改種蜜柚和其他經(jīng)濟(jì)作物,有的干脆荒在那里長草,,這里的田野不是原來的田野,,這百頃連片的田里我看不到一個勞作的身影。田地可以自由轉(zhuǎn)讓了,,即使看到了那忙碌的身影也不定是田地的主人,,多半是雇工。
一進(jìn)村,,村莊只有老鳳婆一人坐在操場上曬太陽,。小時候,她是最閑不住的人,,田間地頭不斷地忙碌,,身體好得很,從未見她生過病,,如今可能也病得厲害,,她佝僂著身軀,一手打遮著眼仔細(xì)瞧我,,她是從我的招呼聲才辨別出是我來,。村前那口池塘不養(yǎng)魚了,成了一畦死水,。那一排草垛也舊了,,架上幾年沒添新草了,舊草都爛成灰顏色,,像頂著一頂灰斗笠,,這一排草垛遠(yuǎn)遠(yuǎn)望去,像是為村莊站崗的最后稻草人,;只是草垛下沒有一頭牛,,這個村莊沒有一頭牛,連村后那片梯田也見不到一棵水稻,沒有田可耕,,還要牛干什么,?
整個村莊除了老鳳婆我沒遇上其他人,村莊靜得可怕,,十有八家房門緊閉,,沒有人間煙火熏燎的村莊,被風(fēng)雨剝蝕得特別的舊,。大伯家屋脊上那快要脫落的灰瓦,,懸在屋頂?shù)臍堥苌希o(jì)公家那扇風(fēng)一吹就會唱歌的木門,,哀哀地鳴著,,老屋院前那段被風(fēng)揭去瓦蓋的圍墻,像日漸消融的冰雪,,一寸寸地向地面消融,生產(chǎn)隊那一排牛圈早沒了影子,,連村頭我們家的蘑菇房也沒了蹤跡,,我聽到地底野草歌唱的聲音。
我親愛的五叔,,這個昔日的種糧大戶,,分田到戶,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以來,,十里八鄉(xiāng)的第一個年產(chǎn)萬斤糧,、上過報紙的光榮代表,春節(jié)過后還忙著播種,,準(zhǔn)備再種幾畝地,。孩子們出門了,他自己老了,,種不了萬斤糧了,,但種它一二畝地,夠人與牲口吃食他根本不在話下,。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兩個上學(xué)的孩子,,他一個人可以隨意種上全村人的田,他挑村前屋后最近的田地耕種,。五叔有句至理名言:世界上最美的景色就是金黃色的田野,,這沉甸甸的稻穗,比世上任何花朵還要美麗,。
五叔犯不著這么作踐自己,,他的七個孩子都早已成家立業(yè),在不同的城市謀生,他家的日子不犯困,。但他這代人對饑餓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曾聽父親說,五叔小時候趕上一場大饑荒,,跟大人一塊吃樹皮,、草根、還有粗糠,,樹皮,、草根還有粗糠在他肚里結(jié)硬團(tuán),拉不出來,,是奶奶拉他到河邊用手指慢慢地把它摳出來,,讓他撿回一條命。挨過饑餓的人從來不仇恨田地,,他們對糧食有著更為虔誠的感情,。饑餓成了生命最深處的潛意識恐懼因子,他這代人敬天地,,愄鬼神,,說到底,這是心靈深處對土地的最大虔誠,。五叔說,,除非他死,否則他就會種田種到底,,他家的倉廩不能沒有剩糧,,倉里沒糧他心慌。五叔一語成讖,,春節(jié)后不久就病癱了,。如今只剩他們一對老夫妻留守在家中養(yǎng)病。
聽到我的聲音,,五嬸攙扶著病歪歪的五叔起來,,少有人來,連家中那茶盤都銹上一層厚厚的垢,。五叔說,,這十余戶人家留在村里,大家聚一桌吃飯還坐不滿,,“都走了,,都飛到城里了,只剩我們這些落翅的老鴰,,留在家里等日子……”五叔說得激動又要流淚的樣子,。其實五叔也可以隨孩子進(jìn)城過日子,他也去過廣州兒子的家住過幾天,但他受不了城里的味道,,一進(jìn)城就頭暈,,一回來就好了。
五叔的話讓我想到,,其實城市的繁榮加速了農(nóng)村的蕭條,,那涌動的人群都是農(nóng)村的背影,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他們背井離鄉(xiāng)到城里刨食,,他們是遷徙的候鳥,他們背不動的是一個時代的孤獨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