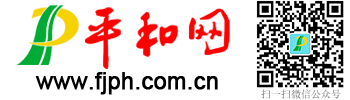共同的鄉(xiāng)音

出門在外,,和人交流總是喜歡普通話。但行走在臺灣,,不經(jīng)意之間,,對方或者聽到你冒出一兩句閩南話,這會有暗號對上的興奮,。
在臺灣桃園大溪鎮(zhèn),,已近黃昏。僅僅是路過參觀,,并沒有停留太久的計劃,。老街的建筑盡管有了西洋的元素,有了改建之后的容顏更改,,但依然有閩南建筑的風格,,恍然就是在家鄉(xiāng)哪個鄉(xiāng)鎮(zhèn)的街道漫步。在林立的店鋪走走停停,,看到一位老人,,坐在一排排的木屐之間,很是慈祥和平靜,,就如家里的奶奶,,那木屐呱嗒呱嗒的聲響從童年的記憶冒出來,在臺灣的黃昏鉤沉兒時的故事,。沒有理由地,我覺得老人應(yīng)該會說閩南話,,就用閩南話和她打招呼“阿嬤,,你吃飽未”。一開口,老人沉靜的表情立刻生動起來,,她說:“原來你會說阮的話啊,。”我故意調(diào)侃“是您說阮的話,不是阮說您的話”,。“是,,是,是,,是咱大家的話”,。老人好像寬容調(diào)皮的孩子一樣,綻放笑容,。我們就在黃昏里的街道上聊天,,沒有在意時間的流逝,直到街道上的燈亮了許久,,我們還坐在街道邊聊天,,那樣的情景就是在老家吃完飯的傍晚,坐在門前隨意閑聊,。“阮阿公是從福建平和大溪過臺灣的啊,。”老人對故地的了解很清楚,“鐵鍋,、豆干,、大溪米粉是阮阿公輩從大陸帶過來,是他們當時的‘賺吃步’(謀生的手段)”,。當年大溪的村民從福建平和歷經(jīng)艱辛來到臺灣,,家鄉(xiāng)的手藝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chǔ),他們就依靠這些手藝在臺灣站穩(wěn)了腳跟,,開始了他們的生活,,聚集而居繁衍后代,生存下來了,,居住的地方總要有個名稱,,于是家鄉(xiāng)的地名就在這里成為新家的地名。大溪,,就是以如此的方式在海峽兩岸繁衍發(fā)展,。
大溪豆干傳人面對中央電視臺的采訪,“我們的豆干其實是來自福建,,來自福建平和”,。對淵源的追溯是對記憶中鄉(xiāng)愁的撫摸,可以消解沉浸其中的傷痛,。清代曾任福建巡撫的王凱泰在一首詩中說:“西風已過洞庭波,,麻豆莊中柚子多,。往歲文宗若東渡,內(nèi)園應(yīng)不數(shù)平和,。”王巡撫的詩解讀了臺灣麻豆文旦柚和福建平和琯溪蜜柚兩柚一條根的歷史淵源,,當我們在臺灣行走的時候,有不少人就和我們聊起平和琯溪蜜柚,,聊起臺灣麻豆文旦柚,,就好像說起大家都熟絡(luò)的兄弟,有了共同感興趣的話題,。
不僅僅在大溪,,也不僅僅是柚子。在臺灣十天,,經(jīng)常會碰到講閩南話的場合,,那種興奮的表情不能簡單理解為生意手段。即使不買東西,,即使不是開店的人,,都會有“咱講同樣話,咱是一家人”的感慨,。
“咱厝出足多名人”,,在臺灣,沉浸在閩南話鄉(xiāng)音之中,,這也是經(jīng)常被提起的一句話,。“以前出的臺灣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林爽文,阿里山神吳鳳,,臺灣望族霧峰林家,,現(xiàn)在有江丙坤,還有林毅夫,,足多有名人,。”用鄉(xiāng)音說起同樣的榮耀,親切也就不容置疑,。
“咱大家來唱一條,。”在和同鄉(xiāng)會宗親吃飯的時候,這個提議得到大家的熱烈響應(yīng),,有人坐,,有人站,有人用筷子擊碗,,有人用手輕拍桌面打節(jié)奏,,男女老少同唱閩南語歌曲《愛拼才會贏》,一杯杯家釀的米酒更是讓人感受鄉(xiāng)音的魅力,,沉浸在鄉(xiāng)音之中,,有些人已經(jīng)淚花閃閃,,但沒有人覺得難為情,,鄉(xiāng)音,,讓所有人都敞開胸懷,舒展在家鄉(xiāng)的柔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