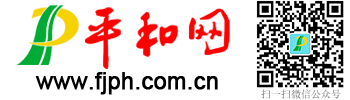語堂的西裝與 魯迅的長衫
魯迅和林語堂是中國近百年來最有代表性的兩位文化巨人,。他們之間的『離合』豈是『恩怨』二字說得清的,。但要說起他們的西裝與長衫,還是有一番來歷可說的,。
林語堂出生于平和坂仔一個鄉(xiāng)村窮牧師家庭,,他的血液里流淌著中西兩股文化基因。一個從小接受西洋文化熏陶的林語堂,,穿著西裝出現在公共視野也就顯得順其自然,。而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從小在傳統文化沃土中長大的魯迅,,一生鐘愛長衫也同樣不足為奇。有趣的是,,林語堂雖然穿得很潮,,觀其一生,他卻是一個傳統的文人,,他的西裝下裹著一個新道家傳統;而魯迅雖長衫一生,,卻又是一個十足的先鋒派,,他的長衫內藏著摧毀舊世界的新思想,二人對比十分鮮明,。
魯迅留日時,,有感于國內同胞之愚弱,立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他棄醫(yī)從文,,以筆為器,展開一場漫長的廝殺,。這時候的魯迅接受了叔本華,、尼采的思想。面對積貧積困,、列強欺壓的舊中國,,魯迅強烈渴望改變這個世界。留日歸來,,胸懷利器的魯迅時刻在關注時局動向,。后來,以陳獨秀,、胡適為首的『新文化運動』一經發(fā)動,,魯迅便毅然投身其中,成為一員主將,。魯迅如一個偉大的靈魂工程師,,把手中的筆,化作鋒利的鋼刀,,先割去日漸潰爛的癰疽,,再剔開表層去刮骨療毒,然后朝著昏昏沉沉的國民一聲驚雷般地吶喊,,讓其靈魂覺醒過來,。這時候的魯迅是穿著長衫的先鋒戰(zhàn)士,沖在中國民主及民族革命的第一線,。
而與魯迅同時代的林語堂為何不先鋒一下呢?按說,,年輕的林語堂在歐美求學多年,那時的歐美正處在工業(yè)全面興盛后走向危機時代,,各種思潮分流涌動——直覺主義與意識流,、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各種學說相繼登場,叔本華,、尼采的唯意志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當代馬克思主義各種思潮席卷世界。然而,,林語堂好像對這些不感興趣似的,。
一九二三年,林語堂取得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后回國當了北大教授,。當時,,國內的『新文化運動』已經分化,以周氏兄弟為首的『語絲派』與以胡適為首的『現代評論派』激戰(zhàn)正酣,,林語堂毫不猶豫地站在『語絲派』一邊,,與昔日有恩于己的胡適他們展開論戰(zhàn)。這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穿西裝的林語堂,,與穿長衫的魯迅并肩戰(zhàn)斗。
然而,,一九二七年是林語堂人生的一個分水嶺,。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恐怖屠殺的烏云籠罩在每一個激進者的頭上,,像林語堂這樣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就從歷史的潮頭急劇跌落下來,。他開始變得沮喪、徘徊,。他不能同魯迅那樣的堅韌者一同前行,,又不愿不能改變自己,最終走上另類獨善之路——這正是魯迅批判的第三條道路,。他徘徊在前進與轉向之間,,人生一下變得尷尬。作為一同右轉的周作人一語道出,,這種尷尬是一種悲劇的角色,。同魯迅及左聯同志們的激情相比,顯得那么不合時宜,。
可以說,,林語堂至此還沒找到自己。那種以筆為刀的廝殺不適合林語堂,。但在動蕩的時代大潮中,,坐下來清談人生又顯得那么另類,為時代所不容,。反過來說,,清談也不是林語堂的初衷,是強作從容的另一種表達,。在那個時代,,作為一個文人,想當一個旁觀者都難,。幸好,,正在徘徊猶豫的林語堂,迎來生命中的一個貴人——賽珍珠,。
一九三六年,,應賽珍珠邀請,林語堂離開飽受戰(zhàn)亂的祖國,,舉家旅居美國,,開始潛心治學,讓他拉開距離重新審視飽經滄桑的祖國,。當他轉過身來時,,他發(fā)現中華幾千年所沉淀下來的文化,是那么的智慧和美妙,。美與丑,,糟粕與精華,他看得更加清楚,。正是這次轉身,,林語堂才真正系統地形成了他的歷史觀、文化觀及他的人生觀,。這是一個成熟的林語堂,,一個沒羈絆的林語堂。從一九三六年旅居美國至一九六六年回到臺灣三十年間,,林語堂的創(chuàng)作進入噴薄期,,他寫出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與靈魂,向西方人系統地介紹了東方中國文化,,贏得了國際聲譽,。這種閑適性靈的筆調,上承老莊,、柳宗元,、蘇東坡,下啟公安,、竟陵,、晚明小品。雖然西裝革履,,雖然身在海外,,但他的根仍在中國傳統的山水哲學之間。
傳統與先鋒,如西裝與長衫,,體現了林語堂與魯迅的本質不同,。魯迅穿著長衫,然而他的紹興花雕酒壺里卻裝著烈性酒;而林語堂穿著西裝,,他的西洋琉璃瓶里卻裝著溫情怡然的糯米酒,。不同的風格,讓我們看到他們的豐富性,。在那個時代,,魯迅和林語堂都交出各自不同的答卷,令后人看到他們各自的選擇——面對中國這樣一個積貧積困的現狀,,他倆各自開出診方,,魯迅直面人生,堅決主張動刀子,,快速去除病灶;而林語堂則從文化自身規(guī)律,,主張采用溫和的中醫(yī)療法,對這個千瘡百孔的世界,,開出一劑撫慰心靈的良方——用傳統的文化去感召受傷的心靈,。魯迅是穿著長衫打西洋拳擊,剛勁兇猛之下,,遍地鮮血;林語堂則穿著西裝在打太極拳,,一招一式,在于強身健體,。魯迅像斗士,,一直沖鋒陷陣,而林語堂更像和平醫(yī)療隊,,在后方開展一場心靈的救治,。然而在魯迅看來,在內憂外患一片廢墟的家園,,還在自己的小天地寫著閑適文章,,多像在炸彈剛炸過的地方,端著一杯咖啡在慢慢品味之后,,說這地方可以種點花草,。而林語堂則認為,筆就是筆,,既不是刀,,更不是槍,在時間的長河里,,藝術文化應該跳出階級的范疇去觀照后人,,這也正是他們本質的區(qū)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