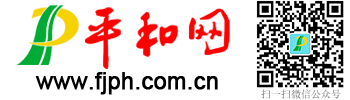一扇歷史的窗口
被時(shí)光淘洗過的每一爿瓷仿佛都是入定的高僧,這經(jīng)烈焰鍛造過的瓷,即使摔成碎片,,仍是不化的舍利,,讓人膜拜,,讓人追尋,。曾經(jīng),福建平和南勝,、五寨一帶的山頭上,,到處散落著無(wú)人問津的碎瓷片,卻突然在某一天驚動(dòng)了世界,,這些碎瓷片背后究竟藏著什么驚世之謎,,引得大批中外專家學(xué)者紛至沓來。
那年五月,,央視《走遍中國(guó)》攝制組也尋蹤而來,。閩南的太陽(yáng)如火一般灼人,下車不久,,裸露的皮膚被曬得通紅,。一條宛如游蛇的機(jī)耕路,斜斜通往山上,。被開墾的山地,,到處都留下鋼爪般痕跡,高低錯(cuò)落的山坡上種滿蜜柚,。
蟬聲嘈雜,,野草沒膝。我和央視攝制組棄車前行,,向遠(yuǎn)處狗頭山走去,。在福建平和五寨鄉(xiāng),山地和溪流,,也都入鄉(xiāng)隨俗地有了阿貓阿狗的俗稱,。一條小溪從山谷奔來,眼前是一汪清澈的潭,。沙灘上留下山洪未帶走的浮柴,,一只紅蜻蜓垂下翅膀停在潭中央的巖石上,還有兩只咬尾的豆娘,,雜技般倒掛在水面的枯枝上,。風(fēng)行水面,,陽(yáng)光搖晃。攝影師眼尖,,沙灘上有一道白光直直刺過來,那是一片瓷的反光,。寂靜的山野,,散落瓷的光芒。
這塊殘片是來自一個(gè)殘缺的盤子,,它的另一半下落不明,。一番清洗,白色釉面上那枚“青花”突然靈動(dòng)起來,,它抖去附著的塵垢,,光潔如鮮。明眼人還是一眼認(rèn)出,,這不是近代遺物,,擱在手里,它沒有打眼的賊光,。這塊殘片歷盡時(shí)光洗劫,,浮光褪盡。歲月已磨去它刺眼的芒,,被歲月捂老的器物,,都將慢慢垂下眼瞼,收斂起逼仄的芒光,,變得日趨柔和,。看到瓷你才明白,,待到一定年齒,,物也會(huì)變得慈祥起來。這塊殘片如一位蒼然老者,,講述著一段幽幽往事,。
殘片邊沿被時(shí)間打磨光滑。攝制組把它擱在一塊大青石上,,殘缺使它失去重心,,隨著它的顫動(dòng),感覺整個(gè)山谷和溪流都搖晃不止,。它,,正是我們此行要尋找的青花瓷,這塊殘片如一道靈光,,閃在一旁引路,。
沿溪流往山上走,,越來越多的殘片撒落地上,撒落在路邊草叢里,,它們似乎要把我們引向一段深藏的謎底,。想起平和博物館成堆的殘片,它們和眼前一樣,,破碎是它們共同的形態(tài),。瓷,這由泥土幻化而來的器物,,像一種命運(yùn)似的,,完整成了一種追求,破碎反成了必然的結(jié)局,。破碎是瓷的宿命,,是它難逃的劫。瓷,,從誕生之日起,,就成了一件需要終身精心保養(yǎng)的“美人”,經(jīng)不起任何磕碰,,越貴重,,越是提心吊膽。然而,,瓷,,也比任何器物都保存得長(zhǎng)久,世上任何東西都難逃時(shí)間的洗劫,,而瓷,,讓時(shí)間凝固。成型那天起,,瓷就拒絕改變,,哪怕最微小的改變,瓷是可以永存的靜物,。
有節(jié)的東西,,都有清亮之音。玉碎,,竹爆,,臨終那一聲響亮過后,便永世緘默,,那份剛烈,,仿佛是對(duì)渾濁世界最后一聲回響。瓷器也具有玉的品質(zhì),,一經(jīng)唱響,,便是隔世的別離,。不管多碎,都是離別前的最后一次合唱,。剛才兩塊殘片輕微磕碰,,我分明聽到一聲召喚,像是重逢后一聲驚喜,。博物館那堆殘片,,還有散落在這漫山之中,甚至天南海北的殘片若是一道重逢,,那將是怎樣一場(chǎng)大驚喜,。
至今無(wú)人知曉這片山坡上還深埋著多少殘片,,泥土之下有著永不為人知的秘密,。但它們一定有出處,每一片瓷都有它出土的窯口,,有它的胞衣“故鄉(xiāng)”,。而眼前這些殘片曾經(jīng)沒有“故鄉(xiāng)”,它們共同流落異鄉(xiāng),,甚至沒有一個(gè)準(zhǔn)確的稱呼,,它們被統(tǒng)稱為一個(gè)洋名字——克拉克瓷。那是一個(gè)被洗劫過的名字,,是一個(gè)落難的船號(hào),。它們需要一場(chǎng)逆流而上的深度尋找,讓這些殘片得以正名,,還原一段塵封的歷史,。
其實(shí),附著于瓷的信息永遠(yuǎn)不會(huì)消失,,無(wú)論是完整,、殘缺或破碎,都是最堅(jiān)硬的存在,。眼前這塊殘片分明是一扇歷史的窗口,,從它現(xiàn)身那一刻起,就把我們引向時(shí)光深處,。我們踏著時(shí)光的碎片一步步走向那段久遠(yuǎn)的青花瓷故鄉(xiāng),。歷史往往始于偶然,有時(shí),,一段塵封的歷史,,就在不經(jīng)意的偶遇之中被開啟。那天,,我們沿著殘片的指引,,開啟《復(fù)活的克拉克瓷》拍攝之旅,,那塊殘片無(wú)疑成了當(dāng)天最珍貴的第一個(gè)鏡頭。在這塊殘片面前,,一切期待都只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