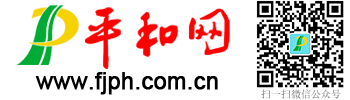林語堂和閩南風(fēng)俗
風(fēng)俗是另外一種鄉(xiāng)音,。每個地方風(fēng)俗有可能存在交會的地方,,也可能顯出不同的特點,這不同,,就成為每個人家鄉(xiāng)的標(biāo)志,,直接或者隱約地透出故鄉(xiāng)的信息。也許閩南風(fēng)俗是在不經(jīng)意之間走進(jìn)林語堂的記憶,,幼小的他不可能在孩童時代就刻意探尋閩南風(fēng)俗的種種,。但這樣的不經(jīng)意又是根深蒂固,盡管歲月流淌,,風(fēng)俗往往在不經(jīng)意之間從記憶之間流露,。恍然之間,,發(fā)覺童年時代的記憶從來不曾走遠(yuǎn),,風(fēng)俗已經(jīng)成為家鄉(xiāng)的一部分鐫刻腦海。
“凡有失足掉在茅廁里的,,必須請一僧人為其換套新衣服,,改換一條新的紅繩為其打辮子,又由僧人給他一碗湯面吃,,如此可以逢兇化吉,。”這樣的風(fēng)俗在閩南,尤其是在平和縣廣為存在,,意為重新有好運,,在流傳的過程中,也有小小的變動,,這大多是根據(jù)家中有什么東西的實際情況,,比如湯面也許就改為一碗煎蛋酒,也就是雞蛋或者鴨蛋煎熟了,,加入家釀的米酒做成蛋湯,,也有的就是來一個白水煮蛋,在剝蛋殼的時候由長輩說一些好話,,寄意為“脫胎換骨”,。當(dāng)然這僧人的角色也未必就是固定,有時候找不到僧人,,或者為了方便,,許多就是就近找個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者在周邊有比較高的聲譽之人代替。林語堂記得這風(fēng)俗是因為他的父親林至誠和母親楊順命擔(dān)當(dāng)過這僧人的角色:“有一天,,我們教會里有一個小童掉在茅廁里,,因為我父親要取代僧人的地位而代之,所以他便要替他打紅繩辮子,,而我母親又給他做了一碗湯面,。”這樣兒時的記憶只是記住了某件事情,但地域的色彩就在不經(jīng)意之間涂抹記憶,,成為多年以后林語堂和閩南眾多聯(lián)系中的一絲,。
不僅僅這簡單的一種風(fēng)俗,其實閩南風(fēng)俗在林語堂的記憶中濃淡不同地存在,。林語堂曾經(jīng)寫過,,男人是不能從女人的衣褲下面經(jīng)過的。這樣的禁忌無關(guān)林語堂的性別歧視,,相反,,在林語堂的生活和作品之中,林語堂對女性的尊重和推崇是他的一大亮色,,如現(xiàn)實的母親楊順命,、二姐林美宮、初戀女友賴柏英到筆下的人物形象姚木蘭,、曼娘,、紅牡丹等等,無一看出他的謙謙君子風(fēng)格,。但對女性尊重和推崇并沒有影響林語堂記住家鄉(xiāng)的這種風(fēng)俗,,從小時候的記憶到成年之后,風(fēng)俗深入骨髓,,然后在某種特定的場合悄然流出,,自然地訴諸筆端,這樣的“潤物細(xì)無聲”讓林語堂銘記到成年之后,,甚至成為告誡他人的律條,,其穿透力不是歲月能夠消弭。
在林語堂的筆下,,閩南風(fēng)俗也并非全部是灰色的色彩,,或者說是沉悶的話題。過年的風(fēng)俗在喜慶的氣氛下穿越林語堂的拒絕直接抵達(dá)他的生活,。“五日內(nèi)全國均穿好的衣服,,停止?fàn)I業(yè),閑逛,,賭錢,,打鑼,放鞭炮,,拜客,,看戲,。”這樣的熱鬧聲稱不是摩登的林語堂曾經(jīng)想置身度外,聲明自己不理發(fā),,不穿新衣服,,只是他的摩登與否無關(guān)年的到來,首先是抵擋不住坐汽車的誘惑而去理發(fā),,然后是因為女傭在春節(jié)前幾天不洗衣服不得不換了新衣服,,之后去買了蘿卜糕、買了走馬燈,,貼了春聯(lián),,點了蠟燭,風(fēng)俗一步一步地進(jìn)入身在國外的林語堂的生活,,林語堂從最初的拒絕慢慢浸入其中,,最后主動拿錢讓傭人去買鞭炮。這不是回歸,,其實風(fēng)俗壓根就沒有從林語堂的記憶中離開,,也許林語堂曾經(jīng)想標(biāo)新立異或者與眾不同的過一個春節(jié),但無需別人勸誡或者什么條令的倡議,,僅僅因為風(fēng)俗,,林語堂就別無選擇,重新納入這個軌道,,過一個中國式,,或者說閩南式的春節(jié)。
閩南文化色彩在林語堂的許多文章中都有涉及,,閩南風(fēng)俗自然也無法規(guī)避,,尤其是在《賴柏英》這本自傳體小說之中,閩南文化色彩體現(xiàn)得尤為充分,,那種閩南話的“直譯”,,閩南風(fēng)俗的直接描述和介入,也許只有閩南人在閱讀的時候能夠最大限度地消除障礙,,換之以會心一笑,。
正如林語堂無法忘懷閩南話一般,林語堂也注定無法忘懷閩南風(fēng)俗,,這些風(fēng)俗悄然進(jìn)入他的生命深處,,融匯在林語堂的生命和文字之中,成為他另外一種鄉(xiāng)音,,時時提醒林語堂故鄉(xiāng)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