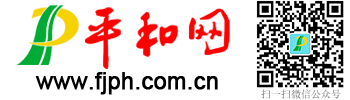十厘米
一種白從四周罩著我,,我再度睜眼時。
我在努力調度自己的感官,它是我伸向這個世界的觸須,,我要以它們重新觸摸這個世界,,找到生命真實的存在。我在努力回放剛才的一幕,,我首先要找到一個回憶的支點,,再以此擴展開來,點,、線,、面,織成一張清晰的網(wǎng),,那些都是我生命存在的真實軌跡,。慢慢的,我看到床頭那桿有些銹跡的鐵桿,,上邊掛著兩瓶藥水,,通過一根細細的白色導管流進我的體內(nèi)。我的意識開始蘇醒,,我準確地知道自己正被搶救,,但我還不知道自己的命還有幾分,是一點一滴地溜走還是回來,?
此時,,我的回憶找到對應的東西,我想起之前我手中有一把大頭鉗,,爬在高高的竹梯上,,當時還要再越上一級梯子,剛好能夠著那捆離高壓線三五尺的電視信號線,。那時我能看清二樓頂上曬的蘿卜干,,在底下扶梯的師傅還叫了我一聲,說不行就讓他來,!我回他說不就差一步嘛,!爬上去,咔嚓剪斷那捆信號線的扎線就完事了,,還費那個勁干啥,。當時我感到梯子有些顫,,又蹬上一級竹梯,,高高舉起大頭鉗,差十厘米就夠著那捆線了,,之后,,像信號突然中斷一樣,一片空白。
我努力搜索那段空白,,我不能讓生命出現(xiàn)空缺,。從高高竹梯上,到醫(yī)院這白色病房里,,生命應該還有一小段距離,,它刻錄在哪里呢?這時,,意識一蘇醒,,疼痛隨之而來,它正一點一滴地從某一個神經(jīng)元傳遍全身,,來證明那些受傷的細胞所受到的全部折磨,。我屈腿,用左腳掐右腳:疼,!再用右腳掐左腳:疼,!我開始兩只手互掐:還是疼!手和腳是神經(jīng)的起端和末端,,我用疼痛檢查自己的受傷程度,,會疼就不會癱瘓;我開始慶幸,,這時,,疼痛是生命最堅實的感覺。這無邊無涯的疼痛,,證明每一根神經(jīng)都還在工作,,起碼神經(jīng)網(wǎng)絡沒受到致命破壞,它就是我感知這世界的全部觸須,。
我想坐起來,,這時身邊的幾個人同時上前阻止。這時我才明白他們剛才一直就在床沿邊守著,。大夫,、單位領導,還有聞訊趕來的幾個親屬,。電視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生命出現(xiàn)垂危時,,只要這三方人在場就可以宣告一個結論,包括生命的去留,。
果真,,大夫宣布了:只是摔壞了骨頭,腰椎壓縮性骨折,,無大礙,,只需臥床靜養(yǎng)。臨出病房大夫還嘀咕了一句:那么高掉下來竟沒死,萬幸,!所有人忐忑的心都有了著落,,只要性命無礙,傷痛無人可以分攤,,大家都放心地離去了,,只留下一個同事臨時照料我,妻來后他也自然交崗了,。
這一跤摔得真不是時候,,距孩子周歲生日僅一星期,妻一下陷入兩難境地,,最后求助于一個好友來幫忙照料幾天,。我不忍心讓朋友留在滿是藥味的病房里過夜,夜里九點便催他離去,。朋友來的頭天,,留下我一人獨自躺在病房里。幾只蚊子從耳邊嗡嗡而過,,它們是夜的主人,,這些醫(yī)院里的蚊子,長期習慣于和人類打交道,,它也學會狡詐,,它先在你眼前盤旋,嗡嗡地試探著,,它要探明目標已經(jīng)睡著了才會下手,,并不像那些沒經(jīng)驗的山間花蚊子,一聲不響,,發(fā)現(xiàn)目標,,撲上就咬,霸道得無所顧忌,;而且不帶麻醉劑直接下口,,疼,出奇的癢,,十有八九都被拍成一攤血,。而此時我還沒睡著,豈能任它宰割,,我早有防備,,見它們飛來,冷不丁地朝它們揮出一巴掌,,它們更警惕,,一下逃之夭夭了。但是它們沒飛遠,,空中繞一圈又飛回來了,;朋友在離去前還為它們布下一道防線,在房間里點燃了一盤青蛙蚊香,,煙霧軟軟盤繞在病房里,,卻不見有半點成效,我和蚊子展開拉鋸戰(zhàn),。
為何蚊香不起作用,,我感到奇怪。這貌似強大的人類,,一旦躺下來,,其實也只是這生物鏈的一環(huán)。我艱難地轉過頭來,,原來是病房里的門沒關上,。只有關上門,蚊香才能發(fā)揮它應有的效力,。而此時我躺在三張病床正中間那床,,離門還隔著一張床,這距離有兩米多,,而此時一動不能動的我,,這咫尺之遙和天上的星星一樣遙遠。此時,,多么希望有個人來幫幫我,,要是能有一個人從病房前走過就好了,我朝門口張望,,苦苦地等待,,不管這個人是誰,只要能聽見腳步聲,,我定會叫住他,,順手幫我把門帶上,就能讓我安生地度過一個漫長的夜晚,。子夜的病房沉寂在夢鄉(xiāng)里,,我能聽清隔壁房間傳來此起彼伏的鼾聲,偶爾還有幾聲沉悶的咳嗽,,剩下就是耳邊蚊子的嗡嗡聲,。
我想大聲呼喊,轉念之間就放棄了,,在醫(yī)院的病房里,,忙碌一天的醫(yī)護人員此時肯定在小憩,,或許還有一兩個掙扎在生命邊緣的病人也沒睡著,但他們也一樣躺在床上動彈不了,,真正能動彈的一定是守在他們身邊的親人,,但他們也一定早已精疲力竭地趴在床沿邊睡著了。
我不能坐以待斃,,一伸手竟碰到床架上的一根鐵桿子,,那是用來掛住點滴的架子,我估摸它加上手臂的長度,,基本上能夠著房門的距離,。我有點欣喜,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我艱難地把它拔下來,,用它來延伸我手的長度,再輕輕地扳轉身子,,努力地探出一點兒身位,,那是我所能做出的全部努力。那桿鐵架子此時在我手中,,比關公的大刀還沉,,我只能憑臂力來推動它在地板上朝房門前進。令我沮喪的是它差房門還有一個巴掌的寬度,,也就十厘米的距離,,那是我無法抵達的距離。我絕望了,,只能任憑蚊子來叮咬,。這十厘米距離是我此時的彼岸,今夜無法到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