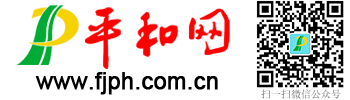桑葚沃若
初見桑葚著實(shí)嚇一跳,,它太像我們南方的毛毛蟲,從形體到顏色一般無二,。細(xì)分之下它還是有很大差別,毛毛蟲毛茸茸的,,每根細(xì)毛如芒尖,,看上一眼就覺心里被扎了一下;桑葚則不然,它像我們閩南一種叫覆盆子的野莓,,擱在眼前有靜物之美,,像微晶體顆粒粘成的。只是野莓如心形,,桑葚如蠶蛹,。果實(shí)如蠶,多有意思的造型,,如把宿命的圖騰永負(fù)枝頭警醒自己,。
同學(xué)告訴我樓下園子里就有兩棵桑樹。翌日清晨,,我在院子角落里找到兩棵結(jié)滿桑果的桑葚樹,。印象中好像都沒見它有過一場(chǎng)盛大的花事,卻在不經(jīng)意間把一樹果實(shí)呈在眼前,,不由得對(duì)它多了一份敬意,。記得初到魯院是個(gè)春寒料峭的日子,只見滿園都是光禿禿的樹,,枝頭上見不到一片嫩綠的葉子,。僅過兩個(gè)禮拜,池邊的柳樹開始吐芽,,一天比一天綠得深。墻院下的玉蘭花也受了蠱惑似的,,開始只是一樹未開的花苞,,幾乎是一夜之間玉蘭花就全開了,粉白,,紫紅,,各占枝頭。玉蘭花事正濃,,滿園梅花開始登場(chǎng),。起初它們像一粒粒布衣紐扣,,顆粒很小,卻很結(jié)實(shí),,過了幾天,,滿園香氣襲來,一樹紅,,一樹白,,艷得很,園子里春深似海,。
花兒競(jìng)相怒放,,課余,同學(xué)們到園子里爭(zhēng)先拍照,。我卻總是對(duì)這兩棵樹心生疑問,,它是誰?別人都忙著追趕春天的腳步,為何它不為所動(dòng),。它個(gè)頭高大,,葉片茂盛,好像它對(duì)春天的花事淡得很,,只記得長葉忘了開花,。或者,,它的花兒開得淡,,開得細(xì)碎,不像玉蘭花,、梅花那樣轟轟烈烈,,那樣妖嬈,壓根兒引不起別人注意,,它在這個(gè)春天被忽略了,。待到謎底揭開一樹桑果時(shí),玉蘭,、梅花都早已謝了春紅,,換了青青梅子,而它那么小的桑果兒藏在密葉間壓根兒不顯眼,。
和這兩棵桑葚一樣不顯眼的是園子里的雕塑,,他們矗立花草下的角落里,所有的雕塑都是深灰色,,泥土的顏色,。或沉思、或交談,、或高歌,,像一個(gè)符號(hào),一個(gè)永恒姿勢(shì)寫盡他們一生的內(nèi)涵,,孑遺在時(shí)間的長河里,。永遠(yuǎn)和泥土站在一起,選擇在花草的角落,,而不是供在廟堂朝拜,,越發(fā)有了親近的力量。有人放言,,當(dāng)下文學(xué),,能燒出舍利子的沒幾個(gè)。魯,、郭,、茅、巴,、老,、曹……哪一個(gè)不是近當(dāng)代中國文學(xué)的巨星,他們無疑是最閃耀的舍利子,。試想,,當(dāng)下能成為中國文學(xué)符號(hào)的又有幾個(gè)?將來,誰能以符號(hào)的雕塑立在這個(gè)園子里?
為文學(xué)夢(mèng)飛翔,,能到魯院來是幸福的,。我們,來自全國各地的五十個(gè)同學(xué),,在各自的文學(xué)路上踽踽獨(dú)行,,在疲憊的中途,如候鳥找到一個(gè)溫暖的湖,,大家一塊交換旅途信息,,一邊梳理凌亂的羽毛,一邊補(bǔ)充所需的營養(yǎng),,為下一站飛行蓄積能量,。到魯院,就像一位修行者到了靈山,,聆聽到最純正的聲音,。魯院請(qǐng)來的每一位老師,都是頂尖一流專家學(xué)者,,每一堂課都為你打開一扇窗,透進(jìn)新鮮的空氣與靈光。
同學(xué)們紛紛感慨,,人到中年,,竟能重回課堂聽老師講課,大家都無比珍惜這寸金的光陰,。除了課堂正餐,,還紛紛成立詩歌、小說,、散文小組,,針對(duì)性地開起小灶加餐。各自選出“領(lǐng)頭羊”,,“領(lǐng)頭羊”各自發(fā)揮能量請(qǐng)來老師與同學(xué)授課交流,,資源共享。魯22的詩歌組同學(xué)最活躍,,他們還成立了魯院第一個(gè)——樹人詩社;小說組人數(shù)多,,占了全班半數(shù)的同學(xué),氛圍很好;相比之下,,散文組相對(duì)低調(diào),,但活動(dòng)精彩。其實(shí)分組不分家,,哪兒精彩,,同學(xué)們就往哪兒鉆,各組總能串到一塊兒,。各組一穿插,,課堂就大了,活動(dòng)排得滿滿的,,大家共同成長,。
獨(dú)木不成林,獨(dú)木也難成參天木,,獨(dú)木風(fēng)必折之;參天木背后定是蔥郁的大森林,,是大生態(tài)。想起散文組就想起組長楊永康,,這個(gè)西北漢子卻長得像和風(fēng)細(xì)雨的南方人,,敦厚、儒雅,。來魯院之前,,他已是一位散文名家,還是國內(nèi)一家著名期刊散文名家專欄編輯,,人脈廣,。他把散文組的十幾個(gè)人攏在一塊,先后請(qǐng)來紅孩、馮秋子,、李曉虹,、王彬、耿占春,、王兆勝,、汪惠仁、劉潔等一大批著名評(píng)論家,、作家,、編輯老師前來交流授課;還把同學(xué)們的散文在《中國散文報(bào)》《青島文學(xué)》《延河》組成專欄刊載,唯獨(dú)他沒放個(gè)人一篇文章,,他真是個(gè)護(hù)林人,。四個(gè)月,每個(gè)組的活動(dòng)滿滿的,,魯院的課堂更是滿滿的,。
寫作是一個(gè)人的舞臺(tái),注定沒有閃光燈,,沒有掌聲,。其實(shí)也不需要這些,需要的只是安靜的一隅,,一方桌,,一臺(tái)電腦足以讓一個(gè)寫作者窮盡一生。寫作本身之外都是身后事,,鮮花與獎(jiǎng)?wù)露际歉郊拥淖⒛_,。課余,我常見永康一人在園子里散步,,或坐在池邊石頭上沉思,,他像池邊一塊落寞的石頭,從不喧囂,。同學(xué)們都不喧囂,,全都沉浸在這安靜的園子里思索。李一鳴副院長說我們魯22安靜得有點(diǎn)過分,,令人不忍,。其實(shí)真正寫作者誰不寂寞?正因寂寞,堅(jiān)持變成赤金般真誠,。
又想起那兩棵桑葚樹,,它似乎真的少了一場(chǎng)盛大的花事,從不爭(zhēng)春,,默默獻(xiàn)上一樹桑果,,從春末到盛夏,,桑葚沃若,滿樹桑果掛枝頭,,每天都有同學(xué)在樹下拾桑葚,,一小盆又一小盆的桑葚成為同學(xué)們最好的牙祭。嚴(yán)冬來臨,,想起魯院,來年春天的桑葚樹下會(huì)有誰?是你?是他?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