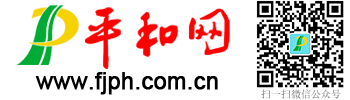自囚與自由
頭一年我住的學(xué)生宿舍位于宿舍區(qū)并列三幢的最后一幢,,與食堂,、教師宿舍樓、圖書館之間并排成為一條直線,。宿舍與食堂之間距離約三十米,,再過去的圖書館相距也就百來米。食堂有一個可同時容納上千人就餐的巨大的長方形餐廳,,餐廳的另一端就是通往教學(xué)樓的水泥通道,,且與第一幢學(xué)生宿舍樓平行。寬敞的餐廳后來被隔出一段作為舞廳,。第一幢學(xué)生宿舍樓住的是學(xué)長們,,他們在樓前與餐廳之間的通道上接待了新生,而后,,在這個公共地段經(jīng)常擺上一張桌子,,一臺黑白電視機為大家播放女排爭奪五連冠之戰(zhàn)??赡菚r候我融不進這個沸騰的大鍋,,因為學(xué)長們安排的電視和座位,我只能在外圍踮起腳尖看,,可憐耳邊雖然灌滿了掌聲和喝彩聲,,饑渴的眼中卻只有一些躍動的人影,我附和人群的熱血和沖動隨著腳酸脖子累而迅速冷卻下來:這些熱鬧不屬于從山里出來的我!就更不用說那個每逢周末就燈光迷離的舞廳了,。
于我而言,,食堂與圖書館都是我進食的地方,食堂打理我的肚子,,而圖書館喂養(yǎng)我的腦子,。于是,,課余時間里我按照學(xué)長的指引,來到了圖書館,。這里是個偏僻的角落,,門前矗立著高大的霸王椰樹和婆娑的鳳凰木,還有冬青圍成的籬笆,。圖書館內(nèi)靜悄悄的,,學(xué)長們或正襟危坐,看書,,在閱讀卡片上急速做著讀書筆記,或起身到借書窗口領(lǐng)取另一本書,,偶爾有一聲椅子搬動的聲音都像是響雷,。但我卻感覺到這里靜悄悄的氛圍中有一股激流在潛藏涌動,于無聲處有一陣陣激烈的喝彩在醞釀,,這里仿佛有一千顆一萬顆古今中外的心在默默交談,,有一千雙一萬雙眼睛在書里書外含情脈脈地對視。第一次進入圖書館,,我空手進去,,空手出來,因為我還沒領(lǐng)到借書證,,我仿佛是個新入行的賊在踩點,,被主人的奢華與典雅所震懾,我相信在這里隨便出手都可以取到令人垂涎的東西,,這里必定是我長期落腳的地方,。
沒過幾天,我的那段簡短得只有三年的閱讀生活開始,,就在那個小窗口,,我的借書卡遞進去,五本書從里邊遞出來,,那情形頗像電影里的囚犯端著鐵盆子走過分飯的窗口,。有位學(xué)長給我開過長長的書單,我讀了其中一部分,,我根據(jù)自己的口味予以取舍,。忘了是什么時候開始,我嘗試著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付諸文字,,竟也陸續(xù)被貼上學(xué)校征文的閱報欄,,又因此獲得了一本特別評論員證件。比之借書證必須在小窗口取有限的五本,,憑此證可以登堂入室直抵心臟,,到森林一般的藏書架前任意挑選,、瀏覽舊書或新書。我的責任就是選擇性閱讀并作出相應(yīng)的評論貼在閱報欄,,把湮沒在海洋中它或它們推介給更多的讀者,,為讀者提供閱讀方向。隨同我去漳州念書的一只綠色軍用挎包此時發(fā)揮了作用,,我珍視機會,,一整套一整套地搬書。
我在圖書館讀書的總時間其實不長,。圖書館太靜了,,稍微一點動靜都會把我從書城中驚醒,而且圖書館終歸是公眾場合,,不可能給你一整塊絕對安靜的時間和空間,,于是我才把書帶回宿舍,強迫自己學(xué)會鬧中取靜的閱讀方式,,舍友的談天喝茶是與我無關(guān)的,。我的下鋪是個帶著1500度近視鏡的家伙,夜里十點熄燈后,,他還點著蠟燭繼續(xù)讀書,,這一點一開始我很反對,我覺得作息時間要動靜分明有規(guī)律才好,,只是后來自己碰上了喜愛得不得了的書時,,也是夜戰(zhàn)到凌晨兩點,直到強迫自己合眼睡覺,,還心馳神往于書中的異域空間,,這才體會了他的心情。宿舍里其他幾位同學(xué)各有自己的閱讀傾向,,偶爾會展開論戰(zhàn),,我是從來沒有參與的。我總覺得自己力量不足,,武器裝備不夠,,不配與人博弈,。我更像一只慌里慌張的猴子,,一直逡巡在詩歌大樹、散文叢林,、小說海洋之間,,急匆匆地采擷營養(yǎng),不管是傷痕文學(xué)還是尋根文學(xué),,不管是鄉(xiāng)土的還是學(xué)院的,,也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
我甚至把文學(xué)類書籍帶到課堂上,把自己埋在喜歡的書頁中,。我非常感謝20世紀80年代中期高校的課堂制度,老師只管灌輸而少有提問,,使我避免了許多未知的尷尬,。我因此每次期末考試時都很緊張,用大約一周的時間翻閱遍整個學(xué)期的必修課,,所幸都能通過。唯一需要補考的科目是古典文學(xué)常識,,當時的助教蔡阿聰老師有一次聊天時告訴我,,“你本來這學(xué)期開學(xué)前要來參加補考的,是林博士說你的古典詩詞欣賞評論文章寫得精彩,,特意給你赦免了。”他若不說,,我竟不知此事,。
過度自囚于感性而柔軟的文學(xué)空間,以致疏忽了對硬性常識的必要把握!然而吉人自有天相吧,,我竟又因自囚而獲自由! 從此我相信,,成天陪伴書本過日的人到達幸福彼岸的方式跟平常不讀書的人是不一樣的。世人皆苦于“心為形役”,,只有讀書人因自囚書城而最終獲得了心靈放飛的多維空間,。自囚到最后的結(jié)果是什么呢?沒人知道,我只謹記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在他的著作《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部開篇之處,,借約翰·米希爾面對新生孫兒克利斯朵夫說的一句話:“好媳婦,,得了罷,別難過了,,他還會變呢,。反正丑也沒關(guān)系。我們只希望他一件事,,就是做個好人,。”
面對浩瀚書海,我們每一個人每天乃至永遠都是丑陋的新生兒,。